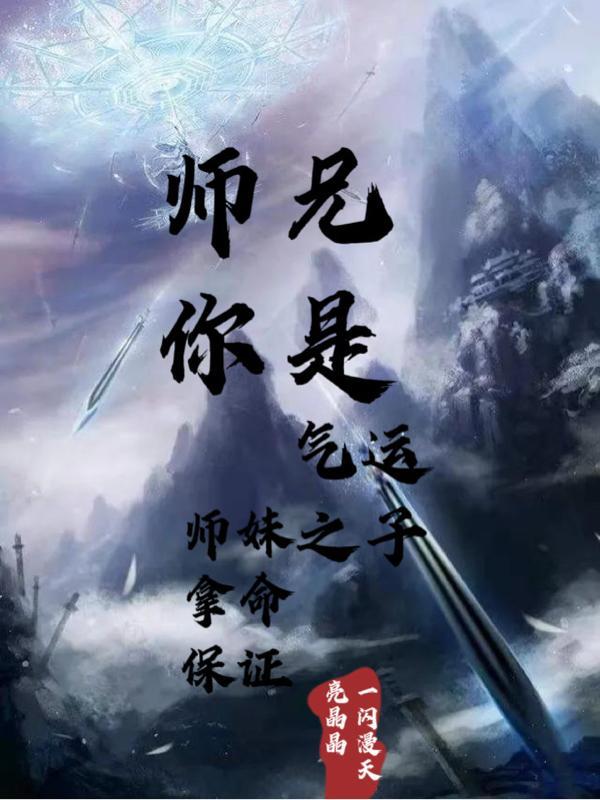紫夜小说>隔壁邻居是山神怎么办 > 我的老师(第1页)
我的老师(第1页)
我的老师
辛萱最後的模样并不好看。
她下葬的日子找人算了,要放在三天之後。
尸体江摆在家中租来的冰柜里,摆上三天,外面罩上厚厚的拉舍尔毛毯,红色妖艳的山花被揉捏到一起,层层叠叠褶皱里也全是漂亮的花瓣。
辛萱一辈子没有结婚,唯一离开麋鹿镇的那几年就是外出上学,回来後就带在麋鹿镇里小学教完,初中缺人就教初中,语文数学教了一轮又一轮。
她小小的个子总是伏在讲台上,埋头涂涂写写,她好像总有改不完的作业本。
金喜露还记得她读初中的时候,性子变得孤僻每次下课也不怎麽走动就坐在位子上,用窗帘遮住自己,观察着辛萱一举一动。
那天作业有点多,她拿着笔的动作早就不知不觉已经开始向辛萱看齐,就连思考时的神态都情不自禁模仿辛萱。
“在干嘛?”
金喜露背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後的辛萱,吓掉了笔,黑色的墨水在书本上砸出了一朵墨水花。
她捡起自己的笔重新握拢,眼眸垂下,又忍不住想要近一点看清辛萱的表情,于是她挪动屁股往後靠了靠,退到背後贴着冰冷的墙壁,无处可躲才敢擡头对视上她凹陷的眼睛。
“啊,我我在写作文。”
金喜露握紧手中的钢笔,还没有察觉到已经笔已经出了问题,握着笔杆闭着眼睛往下戳,一戳黑色的墨水立刻炸了一手,那一页才写完标题的作文纸也没逃幸免。
辛萱年轻的时候眼睛应该是很标准的双眼皮大眼睛,虽然现在眼睛也不小,但深沉的黑色眼睛珠有些浑浊,像一滩不断下陷的烂泥巴。
她盯着你的时候,你正在站在泥巴中央与泥水交缠,下陷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怎麽搞得?走,我带你去洗手。。。。。”
辛萱後面还说了什麽,金喜露已经不记得了,她只记得辛萱拉起她干净的另一只手,将她带离钉住她一整天的木板凳。
她站在教室背後长满青苔的水泥台旁边,不说话也不反抗,仍由着辛萱将她的手拢如手心对着冰冷的自来水冲洗一遍又一遍,她愣愣的模样真像一张不透气的蒸布。
“你最近又和你奶奶吵架了,我也是开了眼界,你奶奶那个和事佬,也就你能激起她的脾气了。”辛萱手上的老茧不比金美玲少,两个人的手搭在一起,金喜露都恍惚了。
“没有,我没和她吵架。”金喜露撇开脸,来往的学生打打闹闹,热闹的说笑声与她们这一觉隐秘的沉默形成对比。
“是,你是没有和她吵架,可你冷战不说话,对你奶奶那个愚笨的人也是一种欺负。”辛萱关上水龙头,擡眼瞄了一眼抿嘴的小姑娘,话并不柔软,依旧是冷刀子直扎人心。
“嗯,你是她叫来劝我的吗?”水声消失了,水龙头年久失修,在金喜露说完这句话,又滴下三两滴。
哒哒,滴——
“不,我是来道歉的。”辛萱话音刚落,上课铃声响了,在操场上疯玩一圈的男生,一个个比赛似地冲进教室。
极度地吵闹过後,耳边的世界渐渐安静下来,然後金喜露听见辛露说:“该和你道歉的不是金美玲,应该是我。”
被奶奶抛弃,阴差阳错被拐到朱家岭一直都是金喜露的心结。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金喜露才意识自己变了,从害怕辛萱,但渐渐地想要了解辛萱,又不想要被她知道,这样的奇怪心理愈演愈烈,她开始无意识地模仿辛萱。
她看书时,总是将头埋得很低很低,像是被书吸进去了,干瘪的手指抚平书角,然後干涩的眼睛轻轻连续眨了几下,又继续看。
金喜露也想努力学习,读书,读书,读书,这个念头写满了她的日记本。
就像辛萱一样考出去。
不管怎麽样,她心中那块想要逃离的野种子早已生根发芽,霸道地占领她的心思,分不出多的去留心金美玲一天天弱败的身体。
辛萱也不是一直都是愁眉苦脸,或是不近人情,她也有高兴的样子。
金美玲去世的前一年暑假,辛萱带着一份包裹来到金家门口,一大早院子里的露水都还没消下去,金家的房门就被敲得乓乓响。
金美玲那天发烧了,躺在床上睡得昏昏沉沉,没有听见敲门声,还是金喜露穿着夏天棉布长袖睡衣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的是辛萱很惊讶。
以为是来找奶奶的,金喜露扶着门面露纠结:“那个辛老师。。。。。。”
她刚开口,就被辛萱激动的大嗓音吓得门都没扶好,不开玩笑,她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辛萱。
“你考上了!”
辛萱披着到肩膀的短发,额头上歪出来四五根白发随着她激动的肩膀颤动,她的声音盖过了隔壁准时打鸣的公鸡,以至于刚睡醒迷迷糊糊的金喜露以为自己幻听了。
再往下看看,辛萱还穿着她深黑色的睡衣,睡衣领口处绣着一大朵开过头的白山茶,脚上的竟然是一双旧拖鞋,手上好像还拿着一个很大的信封,金喜露想:哦,原来辛老师中彩票了。
虽然辛老师中彩票干嘛要第一时间跟自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