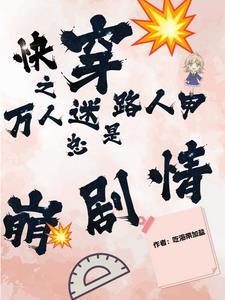紫夜小说>农女双双种田悠闲生活 > 第88章 温饱与浮华(第2页)
第88章 温饱与浮华(第2页)
杨老爹烟锅里的火星暗了暗:
“一亩麦子产一石半,二十亩三十石。秋税要缴三成,春税两成,徭役折银二两,里正摊派”
枯瘦的手指在虚空拨算盘,
“落到手里不过十石粮,够全家嚼用就不错了。”
舒玉掰着手指头算得眼冒金星,忽然瞥见周婆子领着着秀秀在打猪草。老太太佝偻的脊梁像张拉满的弓,六岁的小丫头轻得像片羽毛。
“那年你娘刚过门就得了咳疾,”
杨老爹突然压低嗓门,
“一副药要五钱银子”
舒玉忽然想起元娘妆奁底层那摞当票,最上头那张“银镯一对,当银三两”的墨迹,洇得像化不开的夜。
暮色染红田垄时,舒玉蹲在地头看蚂蚁搬家。杨四嫂子的儿子铁蛋凑过来递了块烤蚂蚱:
“小姐吃么?”
“叫姐姐!”舒玉推回了蚂蚱,她肚子在饿也不能和小孩子抢东西吃。
“还有,这玩意一定要洗干净,烤熟了再吃!”
小丫头盯着姚氏磨出血泡的手掌,突然明白了——她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在温饱面前就像锦缎裹土坯,中看不中用。
“包子铺不需要什么花样吸引顾客。咱家的包子味道就是最好的招牌!只要保持好味道、干净卫生就不会缺生意……”
舒玉看着绿油油的麦田喃喃道。
归途祖孙俩撞见孙寡妇倚着篱笆嗑瓜子:
“哟,杨家小姐也下地?别闪了细腰!”
舒玉突然蹿上田埂,叉腰学颜氏骂街:
“婶子操心自个儿吧!昨儿瞅见您家鸡啄了我家篱笆,正愁没佐料炖汤呢!”
舒玉忽然的反击惊得老母鸡扑棱着上了房梁,留下一地鸡毛在盘旋。
次日县城的铺子里,杨家人忙得脚不沾地。刘秀芝踩着梯子擦匾额,忽然“哎呀”一声:
“当家的!这‘杨记包子铺’是不是太土了?”
“你懂啥!”
杨大川举着扫帚傻笑,
“阿爹说了咱卖的就是实在!”
后厨突然传来巨响。周婆子抱着蒸笼原地转圈:
“少奶奶!这西洋景的灶台咋点火啊?”
元娘盯着三眼灶台直冒汗,她方才差点把引火柴塞进烟道里。还是舒玉冲进来演示她和钱师父琢磨出来的“机关”——拉开风门,填入松针,火折子一晃,蓝汪汪的火苗蹿得老高。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神了!”
周婆子吓得直拍胸脯,
“这灶台怕不是比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火还旺?”
“那是!老夫按着陶窑的火炉改的!”
钱师父得意洋洋的摇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