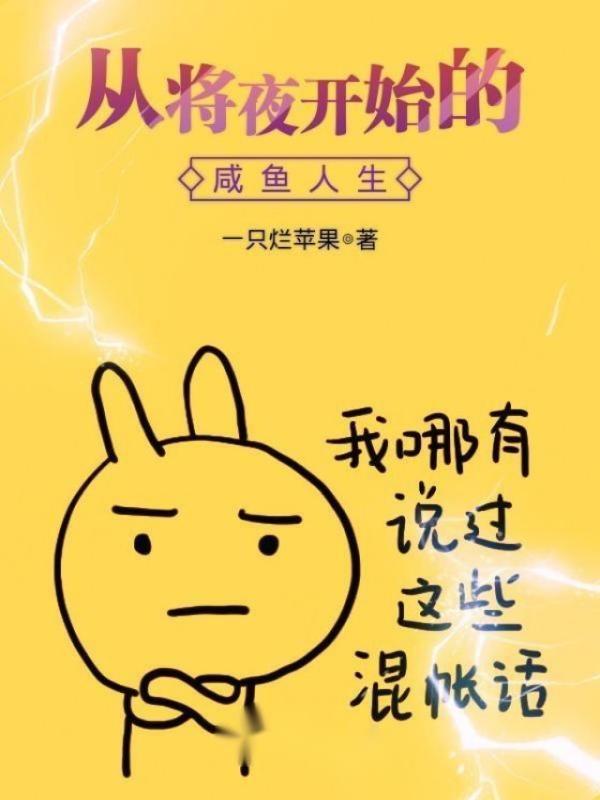紫夜小说>肖想gl离心车免费 > 第 16 章(第2页)
第 16 章(第2页)
眼眶热热的,我拿起桌面上的小镜子,脸还是那张脸,嘴角下撇,比平时惯用的表情更臭了些,除此之外没有异常,完全挤不出一滴眼泪。
我抽出枕头蒙在脸上,逼迫自己装听不见敲门声,它很轻,却一下又一下地锲而不舍,让我烦躁到想蹬被子。
“你还有什麽事?”我拉开门,不用照镜子都知道自己一脸不耐烦,“我睡觉了。”
药膏完全凝固前最好不要穿衣服的,但我懒得说她,不爱惜自己,别人再怎麽干预都是多此一举。
“我睡不着。”
我刚想指着喻舟晚说你大半夜不要莫名其妙敲门打扰别人睡眠,话还没到嘴边,她突然开口。
“涂完药以後更疼了。”
“我又不是医生,”我不愿意多费口舌安慰她,“不行你打车去医院吧。”
喻舟晚堵那里,我不好关门,转身回自己床上倒下,用被子盖住脸,当她不存在。
在我即将要沉不住气探头看一眼时,喻舟晚的脚步声一点一点地靠近,她走得慢吞吞的,躺下的动作更慢,床垫被身体重量压迫时逐渐的下陷几乎是难以觉察的。
我又在被单里憋了许久才掀开一丝缝隙,额头上细细的汗就被空气带出一层凉意。
喻舟晚安静地躺在床的另一侧——不到三分之一的区域,离完全掉下去仅有以厘米计量的距离。
她睡觉习惯蜷起来,显得那块地方更小了。
我分出一半被子为她盖上。
虽然闹到撕破脸的地步,我什麽都不是,至少还能是她的妹妹。
我见喻舟晚一直不动,以为她睡得很沉,可是当我关灯躺下,她却小心翼翼地挪过来,贴着我的背,吸了吸鼻子。
听着像是在哭,但我没有回头看她——这算是半夜被□□的痛苦折磨才感到後悔吗,我在心里暗暗地说了句活该,就这麽被她枕靠着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在我起床之前,喻舟晚已经早早地出去了。
我不知道她去哪了,摸出手机揉着惺忪地睡眼,蓦地想起昨晚被提起的那个“网调Dom”,立马抛弃了给她发消息的念头。
我迅速洗漱一番,去医院打吊针,然後去午饭後去小吴老师那边上课。
她邀请我骑车和她一起逛大学校园,我第一次尝到大学的食堂菜,比七中的可口不止一倍。
“要试试吗?”她把学生卡靠在手机上,“看看你手机能不能绑我的卡,你如果平时想进来自习或者看书都可以。”
我解开锁屏,发现上面有一串未接电话,接连好几个,都是来自同一个熟悉的号码。
“怎麽了?”
回拨,无人接听。
我心里有种强烈不详预感。
半年前的某个雨天,我结束最後一门考试,蹲在校门口,拿着老师的手机连续播打了无数遍杨纯的号码,一直到天黑,一直到老师看不下去,说我先送你回家吧。
“我要去医院。”我说。
後面的记忆像是被曝光过度了,一片空白。
我打车回家,黑灯瞎火一片,踏进家门的一刻,回拨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号码终于通了,我刚把手机放在耳边,没来得及说话,它又挂断。
我倒了杯水灌下去,正打算给石云雅发消息,茶几上的手机嗡的震动了一下,一条微信——来自喻舟晚。
她发了个定位和房间号。
没等输入框里的问号发出去,两条消息被撤回,消失了。
趁着瞬时记忆还留着,我在备忘录里输入了刚才的地址和号码,楼下有直达的地铁,我进电梯时还在犹豫不决是否要去,出了大门,望着逐渐暗下去的天光,我下决心打车。
喻舟晚为我开门,准确来说是拉开一条巴掌宽的缝。
我推门进去的同时立刻在房间里扫视一圈,没有其他人,馀光瞥了眼虚掩的浴室,地砖有斑驳的块状水渍,镜子上的雾气还看得见,证明有人停留过,此时却空空如也。
出于对陌生地方的警觉,我後退了两步,手抵着门板,随时能够逃跑。
我在路上禁不住胡思乱想,甚至在口袋里备了一把美工刀,手指叩响那扇门,我在等待开门的几分钟内幻想了门後许多离奇的场景,比如目睹她和一个陌生人的调教现场,又或者喻舟晚给我发的消息实际上暗藏求救信号……
我在她的注视中踱到床边坐下,短靴踩在地板上的脚步清脆有声。
“你带药了吗?”
房间里热烘烘的,和裹得严实的我相反,喻舟晚身上剩一件单薄的长衫,勉强遮住一半大腿。
我仰头,留意到她的头发湿了,湿得极其不均匀,像是刚从一场阵雨里逃出来。
“没有。”
一个晚上过去,肿起的地方已经消散,青与红的交错却更加张牙舞爪。
“所以你找我来干什麽?”我问她。
热得快出汗了,我脱掉羽绒服抱在怀里,忍不住猜测那条消息是在什麽样的前提下被发送出去的,难道喻舟晚同她的“主人”联络结果错发给了我?可她见到我并没有很惊讶,于是这个理由联同其他的念头一起被否定了。
“去过医院了?”她刻意避开我的问题,摸到我手背上的肤贴。
“嗯,明天再去一天。”
我回答问题时习惯性地转过脸面对对方,碰上的既不是不是关切的问句,也不是重新开啓的话题,而是贴在嘴唇上的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