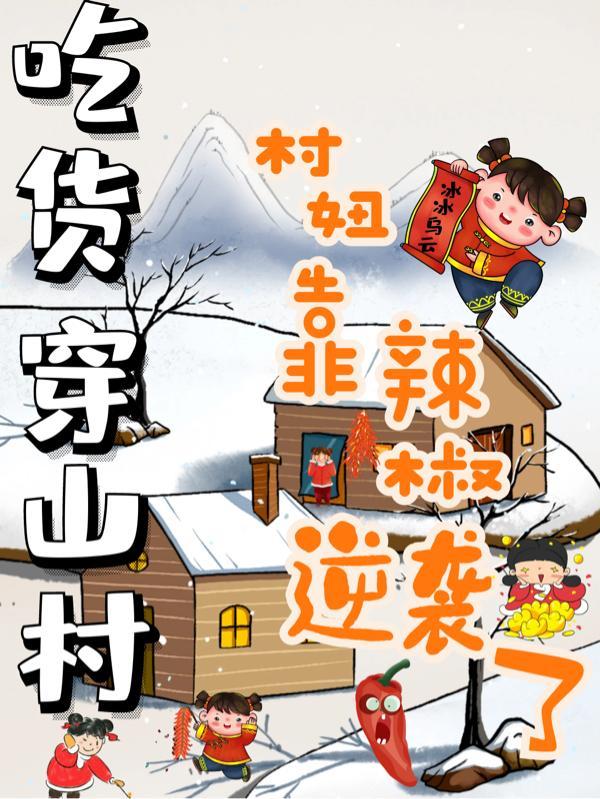紫夜小说>一起数过星星的夥伴是什么 > 雪夜里的毛线团与红对联(第1页)
雪夜里的毛线团与红对联(第1页)
雪夜里的毛线团与红对联
腊月二十四,小年。塘沽的雪下了整整一天,傍晚时总算歇了口气,却把天地间染得一片白。屋檐下挂着尖尖的冰棱,像一串串透明的水晶,风一吹,叮咚作响,倒比新年的铃铛还脆生。
刘若湄刚把吴老师送的酒红色羽绒服挂在阳台晾着——下午试穿时沾了点雪水,她特意铺开块旧毛巾垫着,怕压皱了领口的白毛毛。刚转身,门铃就“叮咚”响了,带着股被风雪冻透的急切。
开门一看,丁念澄抱着个鼓鼓囊囊的毛线筐站在楼道里,眉毛上还沾着雪粒,鼻尖冻得通红,像只刚从雪堆里钻出来的小松鼠。“我妈说小年要扫尘,我趁她收拾屋子,把毛线都带来了。”她挤进门,跺脚时带进来的雪沫子在暖空气里化了,在地板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筐里的七种毛线被她按彩虹色排得整整齐齐,最上面放着副磨得发亮的竹制棒针,针尾还缠着圈蓝线——那是去年刘若湄教她起针时,帮她缠的记号。“你看你看,”丁念澄献宝似的掏出条米色围巾,针脚歪歪扭扭,有的地方紧得勒出了褶,有的地方又松得漏了洞,“织到第三排就乱了,线总缠在一起,我拆了三次,手指头都磨红了。”
她把手伸出来,指腹上果然有几个红印子。刘若湄拉她到沙发上坐,从茶几抽屉里翻出盒护手霜:“先抹点这个,不然该裂了。”说着拿起围巾,指尖轻轻划过那些笨拙的针脚——每一针都带着使劲的痕迹,线绕得特别紧,像怕它散了似的。“你看这里,”她拿起棒针示范,“绕线时松一点,就像写毛笔字要藏锋,太用力反而僵了。你看这针,是不是像你写‘捺’画时总忘了顿笔?”
丁念澄盯着她的手,忽然笑了:“还真是!上次写‘之’字,你就说我捺画太飘,像被风吹跑的。”
窗外的雪不知什麽时候又开始下了,簌簌地打在玻璃上,像有人在外面撒糖霜。丁念澄凑过来学,发梢蹭到刘若湄的胳膊,带着股雪花的凉气。“对了,”她忽然从兜里掏出张折叠的红纸,边角都被冻硬了,“李沐夏让我给你带的,她说这是她爸写的春联,特意挑了副最好的给你。”
红纸展开,墨字在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光泽:“东风吹雪千家暖,瑞气临门万户春。”笔锋里带着股跳脱的活泼劲儿,捺画收笔时故意甩了个小勾,像李沐夏笑起来时歪着的嘴角。“她怎麽不自己来?”刘若湄把春联抚平,小心地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正好能看见下面压着的课程表——那是刚入学时,丁念澄帮她抄的,字迹娟秀,现在边缘已经磨卷了。
“她爸让她去贴年画呢,”丁念澄的棒针终于顺了点,线不再打结,“说老家规矩,小年得把财神爷贴在正对大门的地方,晚了就‘跑’了。对了,桥沐遥说除夕上午来接你,她爸的车能坐五个人,咱们一起去吴老师家。她还特意问你爱吃甜口还是咸口的饺子,吴妈妈说两种都包。”
毛线在两人指间慢慢游走,米色的线团滚到沙发底下,丁念澄伸手去够,忽然摸到个硬纸筒。“这是什麽?”她拖出来一看,是卷成筒的宣纸,标签上印着“洒金红宣”,边缘还沾着点墨渍。
“吴老师送的,”刘若湄拿过纸筒,抽出一张铺开,金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像撒了把碎星星,“说写春联正好,本来想等你们来了一起写。”她从笔筒里挑出支大白云笔,蘸了浓墨,“你想写点什麽?”
丁念澄眼睛一亮,往手心呵了口气:“我写‘学业进步’!给我弟的,他总说我字比他好看,这次要让他心服口服。”她拿起笔,手腕抖得像风中的芦苇,墨点在纸上洇出个小坑。“不行不行,”她把纸推开,“还是你先写,我照着学。”
刘若湄笑着蘸了墨,笔尖悬在纸上:“那我写‘平安喜乐’,给吴老师家添副小的,贴在厨房门上,保佑红烧肉越炖越香。”笔锋落下,横画如平坡,竖画似立竹,藏锋收笔时带着点俏皮的弧度,倒不像平时写楷书那麽板正。
丁念澄看得入了神,忽然说:“你写的字,像你这个人似的,看着清清爽爽,却让人觉得暖和。”
墨汁落在红宣上,晕开温柔的弧度。丁念澄的“学业进步”写得歪歪扭扭,“进”字的走之底还拐了个多馀的弯,却比任何工整的字都热闹;刘若湄又写了副“梅开雪映千门晓,竹报春归万户欢”,打算留给自己贴在宿舍门上。窗外的雪又大了些,把路灯的光晕晕成毛茸茸的圆,屋里的暖光映在玻璃上,和外面的雪光融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家。
“对了,”丁念澄忽然咬着棒针笑,嘴角沾了点毛线头,“薄若柠说她学会做雪花酥了,除夕带两盒来,说要配着吴妈妈的红烧肉吃,甜咸搭配才不腻。她还问你要不要带本书去,说吴老师家有个壁炉,烤着火看书最舒服。”
“那我把吴老师给的糖炒栗子带上,”刘若湄把写好的春联晾在暖气片上,金粉被烘得更亮了,“上次吃的迁西板栗,甜得粘手,正好配雪花酥。”她忽然想起什麽,从衣柜里翻出个布袋子,“还有这个,给你们带的。”
袋子里是七只布偶兔子,都是她用旧毛衣改的,有的缺了只耳朵,有的歪了嘴,却是她攒了半年的功夫。“本来想绣上名字,”她有点不好意思,“针脚太丑,你们别嫌弃。”
丁念澄拿起只歪嘴兔子,塞进毛线筐最底下:“才不嫌弃!我要那个缺耳朵的,像我上次摔破的水杯,有纪念意义。”
毛线团在沙发上滚来滚去,像群圆滚滚的小兽。刘若湄看着丁念澄认真学绕线的样子,忽然想起刚入学时,这姑娘总躲在教室最後排,递作业本时手都在抖,说话细得像蚊子哼。而现在,她敢大声笑,敢把歪扭的围巾拿出来请教,敢叽叽喳喳说遍所有人的打算——原来温暖是会传染的,像这毛线,绕着绕着,就把七个人的心,织成了团再也拆不开的暖。
雪还在下,红宣上的墨慢慢干了,金粉在字缝里跳着碎光。刘若湄把晾干的春联卷起来,和李沐夏送的那副放在一起,忽然觉得这个年,比任何时候都踏实。因为她知道,除夕的餐桌上,会有吴妈妈的红烧肉冒着热气,薄若柠的雪花酥堆在白瓷盘里,桥沐遥爸爸的车会准时停在楼下,丁念澄织到一半的围巾会继续绕在棒针上,还有七个吵吵闹闹的身影,把“家”这个字,写得比任何春联都热闹,都真切。
玻璃上的冰花渐渐化了,映出两个凑在一起的影子,手里的毛线,正一圈圈织着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