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目光所及全是你的唯美句子 > 第151章 公益培训第一站(第1页)
第151章 公益培训第一站(第1页)
第章:公益培训第一站
越野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窗外的风景早已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换成了层层叠叠的青山与错落有致的土坯房。苏念放下手中的考古地图,揉了揉有些酸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车窗外掠过的梯田上。田埂边偶尔能看到几座老旧的石碾,或是墙角堆放的破损陶罐,这些不经意间出现的老物件,让她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又重了几分。
“苏老师,前面就到青石镇了。”司机老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次特意被请来当向导,他指着前方山谷中一片聚拢的房屋,“翻过最后一道梁,再走二十分钟就到镇中心的文化站,咱们的培训点就设那儿。”
苏念点点头,转头看向身边的团队成员。副驾驶座上的林薇正低头检查修复工具包,她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修复师,专攻陶瓷修复,此刻正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套微型打磨工具;后排的陈默则在整理文物保护手册,他负责木质文物修复,手里的手册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备注,都是针对山区潮湿气候的特殊防护技巧;还有负责金属文物修复的赵师傅,正闭目养神,手指却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挂着的青铜工具,那是他从业三十年来的宝贝。
“大家再检查一下各自的工具,尤其是易碎的试剂和精密仪器,”苏念的声音温和却有力,“青石镇气候潮湿,文物破损情况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复杂,咱们得做好万全准备。”
“放心吧苏老师,”林薇抬起头,脸上带着些许兴奋,“我把恒温箱都检查三遍了,陶瓷修复用的黏合剂和填补材料都妥善存放着呢,绝对不会出问题。”
陈默也合上手册,笑着补充:“保护手册我印了一百份,还特意加了图文并茂的简易操作指南,村民们就算不识字,看图片也能明白大概。”
赵师傅睁开眼,眼中带着笃定:“金属除锈的设备都调试好了,针对山区常见的锈蚀类型,我还准备了几种自制的温和除锈剂,不会损伤文物本体。”
苏念满意地笑了笑。这支文物修复团队是她一手组建的,每个人都带着对文物的敬畏与热爱,这也是她敢于带着大家深入偏远山区开展公益培训的底气。这次公益培训计划,是她筹备了大半年的心血——在之前的一次考古调查中,她现很多偏远山区散落着大量民间文物,这些文物没有得到专业保护,有的被随意堆放在墙角受潮霉,有的甚至被当成废品丢弃,还有的因为村民缺乏保护知识,在自行“修复”时造成了二次损坏。
从那时起,苏念就下定决心,要把文物保护的知识带到这些偏远地区,不仅要免费为村民修复文物,更要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身边的老物件,让这些承载着乡土记忆的文物能够长久留存。青石镇是他们公益培训的第一站,这里交通闭塞,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民间文物,却因为缺乏专业保护,很多珍贵的老物件都在慢慢破损消失。
越野车终于驶进了青石镇,镇子比想象中更古朴。青石板铺成的街道蜿蜒曲折,两旁是清一色的灰瓦土墙,屋檐下挂着一串串晒干的玉米和红辣椒,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柴火的混合气息。偶尔有几只土鸡慢悠悠地穿过街道,看到越野车驶过,扑腾着翅膀躲进路边的巷子里。
镇文化站就坐落在镇子中心,是一座翻新过的老祠堂,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匾,上面“青石镇文化站”五个字已经有些斑驳。文化站的王站长早就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在门口等候,看到越野车停下,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
“苏老师,可把你们盼来了!”王站长约莫五十岁,皮肤黝黑,笑容淳朴,握着苏念的手用力晃了晃,“我这电话都快被村民们打爆了,天天有人来问,免费修文物的专家啥时候到。”
苏念笑着回握:“王站长辛苦你了,这段时间多亏你帮忙宣传筹备。”
“应该的应该的!”王站长领着众人往里走,“咱们这青石镇,老物件可不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几样祖传的宝贝,就是没人会修,眼睁睁看着它们坏,心疼啊!”
文化站的正殿被布置成了临时培训室,靠墙摆着几张长桌,上面铺好了蓝色的防尘布,墙角堆放着村民们提前送来的几件文物,有破损的陶罐、开裂的木盆,还有锈迹斑斑的铜锁。正殿两侧的偏房被改造成了临时修复室,王站长特意让人安装了临时电源和照明设备,还准备了几台除湿机,尽量模拟专业修复室的环境。
“苏老师,你看这样安排行不行?”王站长指着布置好的场地,“要是有啥需要调整的,我马上让人弄。”
苏念仔细查看了一遍,正殿的采光很好,长桌排列整齐,足够二十几人同时学习操作;偏房虽然不大,但通风和除湿设备都到位了,用来做修复工作间正合适。“太周到了王站长,这样已经非常好的,”她感激地说,“麻烦你再帮我们在门口贴个通知,说明天正式开始培训和修复,今天下午我们先整理场地,有村民想提前送来文物也可以接收登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没问题!”王站长立刻转身吩咐工作人员去办,临走时还不忘叮嘱,“中午我让人杀了自家养的土鸡,炖了汤,咱们山里没啥好东西,苏老师你们可一定要尝尝鲜。”
团队成员们立刻投入到场地整理中。林薇和陈默负责摆放修复工具,将陶瓷、木质、金属文物的修复工具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不同的长桌上,每种工具旁边都贴上了标签,注明用途和使用方法;赵师傅则在调试除湿机和照明设备,确保修复环境的温湿度符合要求;苏念则开始整理登记表格,准备为村民送来的文物建立详细档案,包括文物名称、材质、破损情况、持有人信息等。
刚忙活了没多久,门口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位头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手里抱着一个用蓝布包裹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好奇地探头探脑。
“请问,这里是免费修文物的地方吗?”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几分不确定。
苏念连忙迎上去,扶住老人:“大爷,您慢点走,这里就是公益文物修复培训点,不仅能免费修文物,还能教大家怎么保护文物呢。”
老人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颤巍巍地打开怀里的蓝布,里面是一个破损的青花瓷碗。碗口缺了一大块,碗身上的缠枝莲图案也有些模糊,碗底还沾着不少泥土。“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有一百多年了,”老人抚摸着碗身,眼神里满是爱惜,“前几年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摔了,我一直想修,可咱们这山里没这本事,城里的修复店又太贵,实在舍不得。”
苏念接过瓷碗,仔细观察起来。这是一只清代中期的民窑青花瓷碗,虽然不是官窑精品,但胎质细腻,青花色沉稳,碗身上的缠枝莲图案绘制得颇为精致,具有一定的民俗文物价值。碗口的破损处有明显的磕碰痕迹,边缘还有细小的裂纹,碗底的泥土已经干结,需要小心清理。
“大爷,这碗能修,”苏念抬头对老人笑了笑,“而且修复后基本能恢复原貌,平时用来观赏或者轻度使用都没问题。”
“真的?”老人眼睛一亮,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那可太好了!苏老师,真是麻烦你们了,我还以为这碗彻底废了呢。”
“您别客气,保护这些老物件是我们应该做的,”苏念拿出登记表格,“大爷,您告诉我您的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我给这碗做个登记,然后咱们先做修复前的检测,明天开始修复的时候,您也可以来看看,我教您怎么简单保养这类瓷碗。”
老人连忙报上信息,旁边的小男孩拉了拉老人的衣角:“爷爷,我也想来看修碗,我想知道这个破碗怎么变好看。”
“可以啊,”苏念笑着摸了摸小男孩的头,“明天我们的培训从上午九点开始,不仅修文物,还会讲文物保护的知识,你要是感兴趣,也可以来听。”
小男孩用力点点头,眼睛亮晶晶地盯着那个青花瓷碗,仿佛已经看到了它修复后的样子。
登记完老人的瓷碗,苏念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铺着软布的收纳盒里,做好标记。刚忙活完,门口又涌来了几位村民,有的抱着破损的木箱,有的提着锈迹斑斑的铜壶,还有的扛着一根雕刻着花纹的木梁,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神色。
“苏老师,我这木箱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上面的花纹都快掉光了,还能修吗?”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暗红色的木箱,木箱的边角已经磨损,箱盖上的牡丹花纹有些地方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木头本色。
“我看看,”苏念接过木箱,轻轻打开,里面铺着一层旧棉絮,“这是樟木箱,材质很好,花纹是浮雕的,虽然有些脱落,但主体结构没坏,修复起来不难,还能保留它原有的韵味。”
“太好了!”中年妇女松了口气,“这箱子以前用来装衣服,防虫防潮,现在坏了,我都舍不得扔,一直放在储藏室里。”
“您做得对,”苏念一边登记一边说,“樟木本身就有防虫的功效,这种老樟木箱不仅实用,还有收藏价值,修复后好好保养,还能再用几十年。”
另一边,陈默正在接待一位扛着木梁的老人。那根木梁约莫两米长,上面雕刻着卷草纹,一端已经开裂,还有几处虫蛀的痕迹。“这是我家老房子的房梁,”老人说,“老房子去年漏雨,房梁受潮就裂了,我舍不得扔,想着说不定能修修,以后给孙子留个念想。”
陈默仔细检查着木梁:“大爷,这木梁是榆木的,质地坚硬,虽然有开裂和虫蛀,但没伤到核心结构。我们可以先用防虫剂处理虫蛀的地方,再用专用的木材填补剂修复裂缝,最后再做个防潮处理,就能保存下来了。”
“真能修好?”老人有些不敢相信,“我以为这裂了的木头就没法弄了呢。”
“可以的,”陈默耐心解释,“木材修复主要是先处理隐患,再进行修补,还要做好后续的保养,只要平时注意防潮防虫,这木梁能保存很久。”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赵师傅那边也忙了起来,一位村民拿来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锁和一个铜壶,铜锁已经完全打不开了,锁身上布满了绿色的铜锈,铜壶的壶嘴也有些变形。赵师傅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着铜锁:“这是民国时期的铜锁,工艺还不错,锈迹虽然多,但没伤到锁芯,我先除锈,再调整锁芯,应该能恢复使用。”
他一边说,一边拿出特制的除锈剂,用棉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铜锁上的锈迹,不一会儿,铜锁表面就露出了原本的黄铜色泽。村民看得啧啧称奇:“赵师傅,您这手艺真神了!这锁我以为早就废了,没想到还能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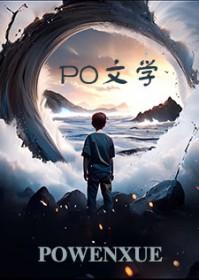
![绝地科学家[综英美]](/img/22197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