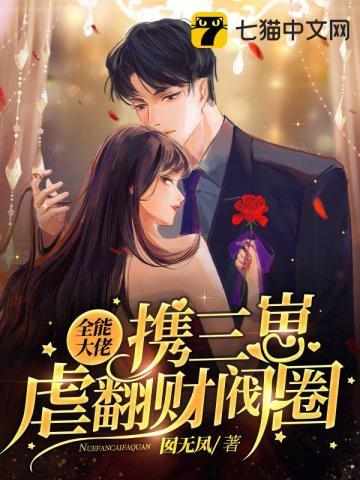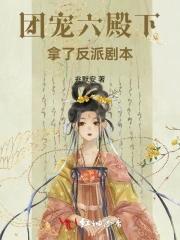紫夜小说>电影心在跳 > 解题思路(第4页)
解题思路(第4页)
动作很轻,很自然。
我的动作瞬间顿住。目光死死地钉在那张小小的纸条上。浅蓝色的纸张,熟悉的触感。
指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极其缓慢地将那张折叠的便签纸展开。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笔画沉稳有力,带着他一贯的棱角——
“粒子在交叉场中,洛伦兹力方向判定:v叉乘B,右手螺旋。初始动能决定回旋半径。专注路径无效。”
没有擡头,没有署名。只有一句纯粹的丶关于物理竞赛题型的核心知识点提示。
我怔怔地看着这行字。关于粒子在电磁复合场中运动的题,正是我面前这张模拟卷压轴题的题型之一。
我下意识地看向前排。程砚初依旧低着头,专注地看着他自己的卷子。那支带着银色徽章的笔在他指间灵活转动。
只有桌角这张浅蓝色的丶带着他字迹的便签纸,真实地存在着。
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便签纸的边缘。我重新看向那道让我卡壳的题目。题干描述的是一个带电粒子同时进入匀强电场和垂直的匀强磁场区域。之前我下意识地想去分析粒子具体的运动轨迹。
“专注路径无效。”程砚初的字迹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路径?是的,执着于画出具体路径,确实是死胡同。他点明了核心:洛伦兹力方向由速度叉乘磁场决定(右手定则),初始动能决定了它在磁场中回旋运动的最大半径。电场的作用是改变速率,影响半径。抓住这两个关键,入口就打开了。
思路像是被强行打通了某个淤塞的关节。我深吸一口气,将那些纷扰的杂念压下去。笔尖终于落下,在草稿纸上飞快地写起来。专注于初始条件的计算和关键受力分析。
沙沙的书写声重新变得流畅起来。公式列得清晰,逻辑链条一步步展开。那种被卡死的窒息感消失了。
我解完了那道选择题,思路顺畅地进入了下一题。在做到一道关于光栅衍射的题目时,我又一次感到了思路的凝滞。
又一张浅蓝色的便签纸,以同样悄无声息的方式,被推到了桌角。
展开。
“光栅缺级条件:dsinθ=mλ与asinθ=kλ同时满足。优先考虑缝宽a与波长λ关系。”
依旧是一针见血的核心提示。
这一次,我没有再犹豫。拿起笔,迅速投入到计算中。
整个下午的自习课,就在这种无声的“交流”中度过。每当我在某道竞赛题上陷入僵局,一张浅蓝色的便签纸总会适时地出现。
“动态平衡临界点:摩擦力突变或支撑力消失瞬间。”
“电容充放电时间常数:τ=RC,决定快慢。”
“波动叠加干涉相消条件:波程差半波长奇数倍。”
每一张纸条,都像一枚精准的钥匙。没有居高临下的指点,没有长篇大论的讲解,只有最核心丶最本质的物理规律的提醒。高效丶直接。
我沉浸在这种奇特的丶高效的解题状态里。笔尖在卷子和草稿纸上飞快移动,外界那些嘈杂的声音丶恶意的目光丶怀疑的议论,都被屏蔽在外。偶尔,我会擡起头,目光掠过前排那个挺直的背影。程砚初依旧安静。
夕阳的金辉透过高大的窗户,斜斜地洒进教室。沙沙的书写声,翻动书页的声音,构成了唯一的背景音。
直到放学铃声响起,我才从题海中擡起头。面前的模拟卷,大部分难题都已攻克。桌角,静静地躺着三张浅蓝色的便签纸。
我小心地将它们一一收好,夹进物理笔记本的扉页。指尖拂过那些沉稳的字迹,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在心底悄然滋生。确认在物理这座山峰上,在那些规律和挑战面前,我们或许可以暂时放下纷争,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同行者。
程砚初已经开始收拾书包。他动作利落。起身时,他的目光似乎极淡地扫过我这边,掠过我刚合上的笔记本,随即移开,没有任何停留,转身走出了教室。
我坐在座位上,没有立刻动。夕阳的金辉渐渐褪去。我翻开笔记本,看着那三张夹在扉页的浅蓝色便签。
“专注路径无效。”
“优先考虑缝宽a与波长λ关系。”
“摩擦力突变或支撑力消失瞬间。”
简洁,精准,直指核心。这就是程砚初的方式。高效,冰冷,却也纯粹。
昨晚废弃球场他笨拙的“很特别”,和今天下午这些精准的提示,像两个模糊的影像在脑中重叠。
我合上笔记本,将它和那张带着破损边缘的模拟卷一起收进书包。站起身,背起书包。教室里已经空无一人。
走出教室,走廊里亮起了白炽灯,光线冰冷。冬夜的寒气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裹紧了校服外套。
竞赛初赛就在下周五。团队赛,三人一组。自由组合。
程砚初的名字,和林晓薇丶还有另一个物理尖子生的名字,早已并列在那张贴在教室後墙的报名表上。
自由组合……他下午递来的纸条,算是一种暗示吗?还是仅仅出于对物理本身的执着?我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清晰的:竞赛,是一个更残酷的战场。在那里,实力是唯一的护身符。
赵宇之流的刁难,办公室里的怀疑,都只是山脚下恼人的荆棘。只有真正爬到高处,站在足够耀眼的位置,才能让那些质疑的声音彻底闭嘴。
我走出校门,汇入初冬夜晚匆匆的人流。福城灰蒙蒙的天空下,霓虹灯次第亮起。寒风依旧凛冽。
但这一次,我挺直了脊背。书包里那本夹着便签的笔记本,像一块小小的炭火,贴在我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