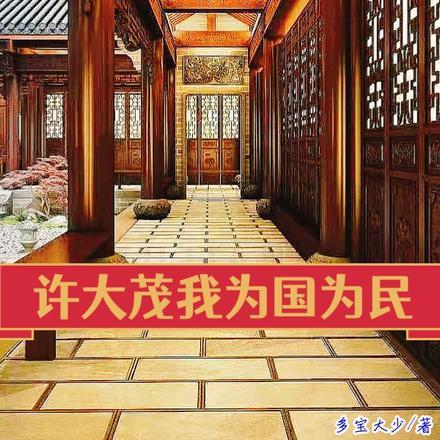紫夜小说>解药的英文 > 番外 小别胜新婚(第3页)
番外 小别胜新婚(第3页)
他师尊平坦小腹一下下突突抽跳着,被掐出指印的脂白腿根也不住颤动,清透液体一股股从紧抽的xue口中喷出,将底下鸳鸯锦洇得一片深红。
云雨暂散,他的手垂落在脸上,遮了一小半秾艳眉眼,泪流沾皓腕。
一年未达到这样的高潮,秦染昏沉了许久方清醒。
却看见徒弟将他两条腿分开压在胸口,以唇舌肆意玩弄他的阴户。
一时气急,将腿放下,含怨望着徒弟:“你方才把我弄成那样。。。。。。”话语低回:“怎麽不出精?”
严珩将他腿重新拉了起来,抚弄他的腿道:“徒弟许久没尝师尊的水,一次想要多点,操师尊胞宫水出得多。”
他师尊的脸覆上一层薄红,簪坠鬓斜,显得更为娇慵:“那你也不能。。。。。。”
徒弟又将他腿擡起来折在胸口,埋首其间含糊道:“师尊等会再说,徒弟还没喝饱。”
“啊。。。。。。嗯。。。。。。啊。。。。。。”轻吟声细。
方被操干得彻底的xue口被温热舌尖捅入,媚肉裹着徒弟舌尖,里头又流出蜜液,悉数到了徒弟不断吸吮的口中。
花xue一开一合,莹润脚趾曲起,被徒弟压在胸口的腿开始因舒爽而轻微颤动,系在脚腕上的小巧银铃随着腿颤,一阵又一阵地响,伴柔媚呻吟,格外动听。
严珩品尝着那嫣红花蕊,终于吮吸个够,才将脸从那片朝思暮想的桃源地移开。
脸虽然移开了,但眼睛还盯着那销魂处,方才素苞早被捣碎,淡粉缝隙变成酥红一线,隐隐微张,蕴藉其中的小巧花瓣红馥馥的,充血外翻。圆润花珠肿大,一颤又一颤。最中间的紧闭xue口已绽,不断翕合,上头沁出几滴蜜露,粉心轻点胭脂。
简直像一颗饱胀的蜜桃,被手指插得软烂,流出香甜汁水。
分明没有半点此前青涩模样,只淫艳无比,诱人提着长枪,将其狠狠蹂躏。
“嗯。。。。。。”随着严珩再次挺入,秦染不禁轻哼,腰臀一上一下颤着。腿间敏感花珠随着徒弟动作被挤往里,而严珩稍微一往外头抽又出来,被压得十分畅快。花径已熟悉另一个主人的巨大,重重叠叠的媚肉死命缠上去不让其离开,严珩心中喟叹一声,手握住身下腰肢,毫不犹疑直冲入底。
底下艳红小xue一阵剧烈抽搐收缩,但也还是吃力艰难地吞吃粗大。“啪”一声,徒弟坚硬耻骨撞在他柔软耻丘上,整根粗壮都进到了他的身体里。
严珩将他的腿放到自己腰侧两边,两手撑在他身侧,温柔地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吻。
可下身又那般凶猛可恶,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开始在xue内狠进狠出,把一口水xue捅得噗嗤作响。
严珩挺着腰在那紧窄花径中全力抽插,只觉得绵软湿滑,他这一年来几番春梦,都是把这人压在身下疼爱,但即使梦如真,怎可及此刻半分销魂?
“哈啊。。。。。。啊。。。。。。。慢些。。。。。。”花径深处涌出水,痉挛着将飞快插干的硕大阳根死死绞住。秦染被他激烈的操干弄得浑身发麻,脚在他的腰际踹了一下。
严珩于是慢下来,轻轻抽顶。
秦染没想到他居然变得这麽慢,腿缠上徒弟的腰,自己擡臀挺腰迎合着身上的冲撞。
臀部一上一下接着徒弟的撞击,秦染收紧花径,将里头粗壮绞紧,不满咬唇:“快点!”
严珩瞧他自己把一饱满屁股送过来,噙着笑一手抓住,沉身一下撞到之前已被撞得微开的宫口里。
“呀。。。。。。”秦染差点被这一撞弄得魂飞魄散,手在严珩背上挠了一把。这下又把臀往後移几分,可被徒弟紧紧抓着,狠狠揉了一下,往他阳根处托。又是啪啪啪响着,鼓鼓涨涨的囊袋一下一下拍在他的臀部上,打得火辣辣得疼。
“珩儿,珩儿。。。。。。珩儿……给我。”身下人娇声念着他的名字,花xue内爱液积压,被阳根搅得滋滋作响。若阳根抽出,便带出一股来,顺着两人交合处流下,有的被撞击拍成白沫,有的把两人阴部浸得湿透,淌到已经湿成一大块的锦被上。
脚腕上的铃铛儿顺着每下冲撞,不停歇地,发出叮当响声。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
两人交缠着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似对交颈鸳鸯,只顾合欢。银铃声儿脆,美人眼儿媚,两条腿颤着夹紧徒弟疯狂耸动的腰,不知射出第几股阴精,高潮数次。
秦染神思恍惚,他微张着唇,满脸汗涔涔,都是被徒弟操出来的,唇瓣一张一合:“珩儿。。。。。。求你快点。。。。。。 要被插死了。”
严珩挺身贯穿他的子宫,弄得身下人又是一颤,一口咬上他的肩膀,在他背上狠挠几记。
他摸着秦染被汗湿的侧脸,偏头喘息,不断吻着他的耳廓:“师尊,徒儿陪您一起死。”
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
愿同死在这鸳鸯衾被上,共偕作,一双风流鬼。
秦染浑身瘫软,被严珩抵在床上猛撞子宫几百抽,最终一股一股射出积压了一年的浓稠精水,打在娇嫩宫腔上。
滚烫的阳精弄得他一瑟缩,宫腔强烈抽搐,蕊心又淅淅沥沥地喷出一道清液。
可真真是,生与死,天上地下,都转了一个来回。
“珩儿,你身上在流血。”
严珩正给他师尊擦着小xue涌出的精水爱液,闻言才觉肩上背上都一阵刺疼,想必是他师尊弄的,擡头回道:“无碍,先擦完这些再处理。”
秦染一脚将他轻轻踢开:“先处理再擦。”他披上外袍便下床给徒弟拿药。
严珩看着他背影,想着师尊还真是,有力时就有力,无力时就绵绵惫懒倒他身上,方才擦他身子时,明明还是雨打琼花一般娇弱。
“珩儿,你先转过身去。”
严珩乖巧转身。
他垂着头,忽然被身後人抱住,在脊背上觉到唇瓣贴上的柔软触感。
然後一只手才开始在抓出咬出的伤口上抹药。
秦染一边涂,一边眼尖发现徒弟嘴角勾起,于是问道:“珩儿笑什麽?”
“珩儿笑师尊属猫。”
秦染起先一愣,随後羞恼:“胡说!哪有属猫的,我属虎。”
“属虎不就是属猫?凶猫。”他转身一下把他师尊搂在臂弯里,捏着他下颌:“师尊在床上叫得和猫儿一样,又喜欢挠徒弟咬徒弟,又喜欢被徒弟摸,可不就是只猫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