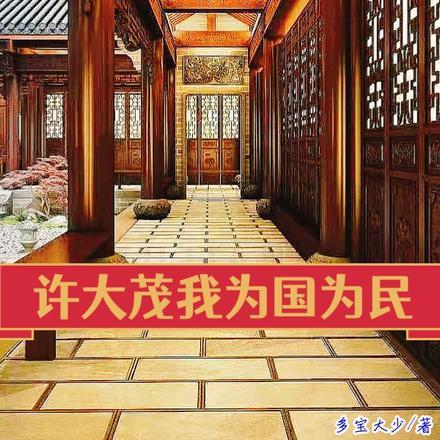紫夜小说>万里江山一梦还是一梦 > 染尽胭脂画不成(第2页)
染尽胭脂画不成(第2页)
官伎生涯刻入骨子里的妩媚谦卑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挺拔与利落。她脸上甚至沾着几点新鲜的木屑。
“家主,您看这个!”她声音清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顾不上行礼就径直走到院中空地,将一直背在身後的一个巨大包袱解开。
哗啦一声,一个精巧的木制模型呈现在眼前,是缩小了数十倍的梁州新城规划模型!
城墙丶街道丶水渠丶坊市丶粮仓丶工坊,甚至预留的医馆丶学堂位置,都清晰可见。榫卯结构严丝合缝,比例精准。
“这是我和营造队几个老把式琢磨出来的。”穗心的指尖带着薄茧,却异常灵活,“您看这引水渠,改了三道弯,省了三百多丈工料!还有这城墙根基,用碎石混着河泥丶石灰夯,比纯用砖石省料一半,更抗洪水冲刷!”
她语速飞快,眼中跳跃着创造的光,“料场那边,新搭的窝棚都加了双层竹篾墙,中间填了干草和碎布头,倒春寒也不怕了!对了,漆渠清淤用的龙骨水车,改进了齿轮,现在三个人就能顶过去五个人的力气!”
阳光勾勒着她侧脸的轮廓。那张曾被脂粉精心修饰丶只为博人一笑的容颜,如今素面朝天,鼻梁挺直,下颌线条清晰有力。汗水在她光洁的额角渗出细小的汗珠,几缕碎发贴在颊边。她整个人像一把刚刚淬火丶锋芒毕现的利刃,又像一块被打磨掉所有浮华丶露出坚韧本色的璞玉。
昔日困于方寸之地的舞袖翩跹,化作了丈量城池丶指挥匠作千军万马的豪迈。她的美,不再是供人赏玩的精致器物,而是充满了力量感与勃勃生机的创造之美。
黎梦还站起身,走到模型前,手指轻轻抚过那微缩的城墙和水渠,她含笑看着穗心那熠熠生辉的双眸,那里面燃烧着不再是取悦他人的火焰,而是改造天地的雄心。
从以色侍人的官伎,到执掌一城筋骨脉络的总匠师,这其中的蜕变,这砸碎旧枷锁丶用智慧和汗水重铸自我的过程,黎梦还和穗心本人一样清楚。
她心中满是欣慰,多少赞扬涌到嘴边,但最後只是化作轻声一句:“好,穗心,做得极好。这新城,便依此模样,由你亲手筑起。”
最後进来的苜安,脚步最轻,像一片羽毛落在青石上。她依旧穿着不起眼的灰蓝色粗布衣裙,发髻简单挽起,插着一根毫无雕饰的木簪。
然而,当她擡起眼,那双曾被深宫阴霾笼罩丶习惯性低垂的眸子,此刻却如浸在寒潭中的星辰,清澈丶锐利,带着一种洞悉世情的冷静。
她走到女主面前三步处停下,没有言语,只是从怀中取出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册子,双手奉上。册子边缘磨损得厉害,显然被频繁翻阅。
“家主,”她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有三件事。”
“其一,盘踞在西山棘阳谷的溃兵残部,首领三人及其心腹共十七人,昨夜丑时三刻,已被元登将军率队尽数剿灭。缴获兵甲丶私盐若干,名单在此。”
“其二,潜伏在长宁渡盐商崔记中的旧世家眼线,共三人,已于今晨借‘验货掺沙’之由被市吏扣押。其传递消息的渠道,是借运酱菜的陶罐夹层。”
“其三,关于南边那位使者私下接触城内几位乡绅的密谈内容,及乡绅们真实态度。”
她说完,就静静垂手侍立,姿态依旧恭谨,却再无半分昔日官奴面对贵人时那种深入骨髓的瑟缩与恐惧。
黎梦还翻开那本沾着些许尘土丶却记录着梁州暗流汹涌的册子。
字迹是苜安特有的,纤细却筋骨嶙峋,带着一种刻入骨髓的警觉。
她擡头,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女子。
苜安的脸庞,是三人中最显清减的,带着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
若不是摘下平日打探消息时候需要的温柔可亲的面具,总会在眉宇之间看到难以完全抹去的清冷与疏离,轻声诉说着当年深宫的幽闭和失去所有亲人的剧痛
然而,在这份清冷之下,却蕴藏着火山般的力量。她的五官其实极精致,尤其那双眼睛,眼尾微微上挑,本是娇柔的底子,却被淬炼得只剩下锐利如刀锋的洞察。
她站在那里,像一株生于幽谷绝壁的兰草,不招摇,却自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韵,在暗影中悄然绽放光华。这种美丽是涅盘重生的丶带着致命吸引力。她不再是任人践踏丶随时可能无声消失的枯骨,她是掌控暗影丶守护光明的无形手。
黎梦还合上册子,目光深深地看着苜安,仿佛凝视着和她有过相似容貌,在深宫夹缝中挣扎求存最终香消玉殒的几个姐姐。
这份沉静如渊丶锐利如匕的气质,让黎梦还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骄傲与怜惜,但她最终什麽也没说,只是伸出手轻轻摸了摸这个十四岁女娃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