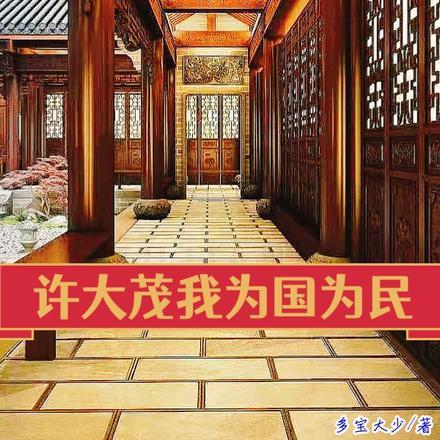紫夜小说>万里江山一梦还是一梦 > 缟袂相逢半是仙(第1页)
缟袂相逢半是仙(第1页)
缟袂相逢半是仙
三日後,淳于法在军帐召见诸将。他伤势未愈,却执意披甲,玄甲下的白麻布隐约渗出血色。案前摊着宇文家潜伏人员的名单,是宇文顺供出的。
“宇文氏馀孽,当一个不留。”淳于坚冷声道。
淳于法却摇头:“主犯当诛,从者可抚。冀州缺矿工,这些人正好充作苦役。”
衆将愕然。按北秦旧律,谋逆当族诛。
淳于坚叹了一声开口,“襄侯仁慈。但宇文顺……”
淳于法截口道,“让他随穆医师学医。以医术赎罪。”
淳于坚猛地看向她,却见他目光澄明,无半分恨意。
他忽然意识到,他不是在救宇文顺,而是在救穆昭,救那个失去儿子十多年的母亲。
“准。”淳于坚,这位抚军大将最终拍板。
散帐後,淳于坚和黎梦还对坐良久,欲语还休。直到案上的油灯爆了个灯花,他伸手去拨,才见拓跋明立在帐外,道袍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响。
“道长还有事?”
拓跋明摇头:“贫道明日啓程,特来辞行。”
淳于坚想说些什麽,最终只道:“保重”
黎梦还送拓跋明出营,两人就这样,沉默着,一前一後走着。
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却始终隔着三尺距离,如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与此同时,腊月的辽泽冻实了,冰面跟铜镜似的,映着骑兵呵出的白气。穆顺勒马停在雪坡上,左脸上那道刀疤叫寒风刮得发紫,旧绷带边儿上渗着浅黄的药渍。
那是三日前在暗河里搏命,宇文震的刀尖挑的。
“穆校尉,高句丽人把白狼口封死了!”斥候喘着粗气,擡手指向前头。峡谷隘口处新起了冰墙,墙头上人影晃动,兽皮裹着的投石机蹲在那儿,像黑乎乎的巨熊。
穆顺眯起眼,琥珀色的瞳仁迎着晨光,泛出铁器似的冷。“冰墙的根基在哪儿?”
“河……河床底下?”斥候答得犹豫。
少年打马冲下雪坡,绛色披风在风里扯得笔直,单骑直逼到敌阵三百步内。
墙头箭雨泼洒下来,他猛扯缰绳,战马扬蹄长嘶,手中长弓已连发三箭。
“噗丶噗丶噗!”
箭镞钻进冰墙底处,炸开三团墨汁似的黑斑。那是他特制的煤粉箭,专为标记用的。
“发信号。”穆顺拨转马头,一支弩箭擦耳飞过,扯断了半截绷带,但他好似无察。
烽燧台陡然升起青烟。峡谷两侧雪坡轰然塌陷,露出早先挖空的坑道。淳于法的冀州铁骑如黑潮涌出,马蹄裹着草毡,踏冰无声,直扑冰墙根基。
“砸!”淳于法挥剑大喝。
重锤朝煤粉标记处猛砸,冰墙应声裂开。
高句丽守军随冰块坠入冰河,惨叫被寒风撕得稀碎。
穆顺立马坡顶,染血的绷带在风中狂舞,像是一面招魂的幡。
半日後,军帐里,穆昭剪开儿子肩头浸血的纱布。箭创已溃烂发黑,腐肉透出甜腥气。她握刀的手稳得像山石,刀刃剜过伤口时,少年浑身肌肉绷得硬,喉间却没漏出半点声响。
“疼就喊出来。”穆昭嗓子发干。
但穆顺只是扭头望向帐外操练的兵士,眼中映着跳动的篝火。
帐帘忽被掀开,小兵捧着烤鹿肉愣在门口。穆昭迅速用净布掩住伤口,起身接肉时,袖口拂落了药瓶。穆顺弯腰去拾,指尖与母亲的手一触即分。
“多吃肉,长筋骨。”穆昭把最嫩的里脊夹给他。
少年默默咀嚼,听着帐外传来《无衣》战歌,调子跑得荒腔走板,却唱得群山都在抖。
正月十六,雪夜。穆顺带着八百死士爬过顶子山,每人背上两袋硫磺粉,靴底缠着防滑的草绳。三更时分,他们伏在山坳上往下看,高句丽的粮仓依山而建,守军正围着篝火烤狗肉。硫磺粉沿冰坡倾泻而下,遇火就燃,爆起幽蓝的焰光!
“敌袭!”惨嚎撕破雪夜。穆顺张弓搭箭,箭头裹着油布点燃,流星般射向最大的粮囤。火舌窜起十丈高,照亮他那张花儿似的脸,如修罗降世。
捷报传回长定那日,穆昭正在伤兵营熬参汤。“穆医师!穆校尉又添新伤!”担架上擡来昏迷的穆顺,左肩插着半截断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