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承爵 > 第62章(第1页)
第62章(第1页)
江澄连滚爬爬地扑过去,抱住他冰冷僵硬的身体,触手所及的硌人骨头让她崩溃大哭。
“哥!我们回家!我带你回家!我们再也不来了!我们回家……”她语无伦次地哭喊着,用力想将他扶起来。
江郁没有反抗,也没有配合,像一具失去所有牵引线的木偶,任由江澄费力地将他架起,踉跄着拖出了这间承载了他最后绝望的木屋。
离开部落,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辗转回国的一路,江郁始终维持着那种令人心惊的沉默和空洞。他不看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不听江澄带着哭音的絮叨,不吃不喝,只是闭着眼,仿佛灵魂早已滞留在了那片冰冷的雪山。
江澄不敢再刺激他,只能寸步不离地守着,偷偷抹泪。
回到国内,江澄没有送他回那个充满回忆的公寓,而是直接将他送进了一家顶级的私立疗养院,环境幽静,安保严密,有最好的心理医生和护理团队。
医生诊断,江郁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重度抑郁,伴有躯体化症状,需要长期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
起初的治疗异常艰难。
江郁拒绝与心理医生进行任何有效沟通。面对医生的询问,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只用极其简短的、没有任何信息量的词语回答。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包括他曾经视若生命的艺术。
药物治疗也效果甚微。那些昂贵的进口药片,似乎无法穿透他内心那堵厚厚的冰墙,只能让他陷入更深的、昏沉麻木的状态。
他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每日在疗养院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对着雪白的墙壁,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他会无意识地用手指在空气中勾勒着什么,眼神专注而空洞,仿佛在临摹一幅看不见的画。护理人员认出,那似乎是某个已故意大利画家的独特笔触。
江澄每天都会来看他,带来他以前喜欢吃的东西,读新闻给他听,或者只是默默地陪着他坐一会儿。她不敢再提起任何与贺凛相关的话题,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可能引发联想的词语。
时间在疗养院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缓慢地流逝。
春去夏来,窗外草木葱茏。
在心理医生持之以恒的、温和而坚定的引导下,在药物和经颅磁刺激等物理治疗的共同作用下,江郁那封闭的心防,终于裂开了一道微乎其微的缝隙。
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零碎的词语,关于威尼斯的雨,关于画廊库房的冰冷,关于……胃痛。
心理医生捕捉到这些碎片,耐心地引导他,帮助他重新梳理和认知那些创伤性记忆。过程缓慢而痛苦,如同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亲手剜开已经化脓的伤口。
江郁常常在治疗中途崩溃,浑身颤抖,冷汗淋漓,像是重新经历了一遍那些不堪回首的瞬间。
但这一次,他没有再彻底缩回壳里。
他隐约意识到,如果不想真的变成一具腐烂的空壳,他必须直面那些鲜血淋漓的过去,必须亲手将扎在心口的毒刺,一根根拔出来。
有一天,在心理医生的鼓励下,他第一次,主动提起了那个名字。
声音很轻,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贺凛。”
说出这个名字的瞬间,心脏像是被电流穿过,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但紧随其后的,却是一种奇异的、仿佛卸下千斤重担的虚脱感。
心理医生没有追问,只是安静地等待着。
江郁垂下头,看着自己苍白消瘦的手指,沉默了许久,才用干涩的声音,极其艰难地,开始讲述。
讲述那些被他刻意遗忘、扭曲的细节。
讲述贺凛那些笨拙而执拗的付出。
讲述他自己因为恐惧和骄傲,而做出的、一次又一次伤人的选择。
讲述总督府廊台上,那句让他悔恨终生的“你消失啊”。
讲述他看到杂志照片时,那种灭顶的绝望和自我厌弃。
他说得很慢,时断时续,逻辑混乱,常常因为情绪激动而无法继续。
心理医生始终耐心地倾听着,引导着,帮助他看清那些被情绪掩盖的真相——贺凛的爱并非枷锁,而是他因为自身的不安全感而将其视为了束缚;他的放手并非不爱,而是另一种更沉重的、带着绝望的成全。
“他值得更好的。”江郁最后,喃喃地说出了这句压在心底太久的话,眼泪无声地滑落,“是我不配。”
心理医生看着他,温和而坚定地反驳:“感情里没有配不配,只有愿不愿意。江先生,你惩罚自己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了江郁心上。
他怔怔地抬起头,看向医生。
他惩罚自己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用自我放逐,用濒临死亡,用行尸走肉般的活着……
可这惩罚,除了让他和关心他的人痛苦之外,又换回了什么?
那个人的回头吗?
那个人已经向前走了,走得很远,很好。
他还在原地,用自己的痛苦,祭奠着一段早已被对方放下的过去。
多么……可笑。
从那天起,江郁的治疗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开始积极配合,按时服药,主动参与疗养院组织的艺术治疗和体能恢复训练。
他依旧瘦弱,但眼神里,那层厚重的、死寂的灰翳,似乎在一点点褪去,偶尔会闪过一丝极淡的、属于思考的光。
他重新拿起了画笔。
起初只是机械地涂抹,后来,他开始尝试画一些东西。不再是以前那些充满张力和隐喻的创作,而是一些极其简单、平静的景物——疗养院窗外的树,护士端来的水杯,甚至只是阳光在墙壁上投下的光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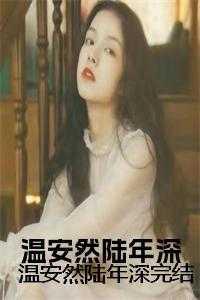
![肝帝无所不能[全息]+番外](/img/233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