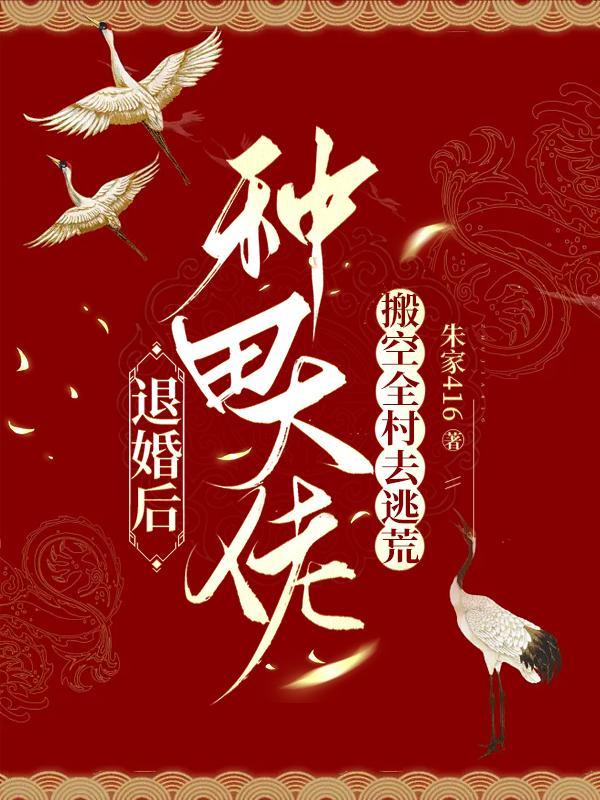紫夜小说>承爵是什么意思 > 第26章(第1页)
第26章(第1页)
拍卖预展那天,贺凛去了。他穿着低调,混在专业的收藏家和评论家中间,在一件件展品前驻足。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那幅压轴巨作前。画布上充斥着大胆、冲突的色彩和近乎暴烈的笔触,却在混乱中构建出一种惊人的秩序感和蓬勃的生命力,与江郁身上那种沉静外表下隐藏的坚韧不拔奇异地契合。贺凛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不是用投资者的眼光衡量价值,而是试图去感受江郁在这幅作品背后所倾注的心血与信念。
他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打量目光,有些是好奇,有些是探究,毕竟“贺凛”这个名字出现在这种纯粹的艺术场合,依旧显得有些突兀。但他浑然不觉,全部心神都沉浸在与作品的无声对话里。
拍卖会当晚,气氛紧张而热烈。贺凛没有选择显眼的包厢,而是坐在大厅后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能看到前排江郁的背影,挺直,安静,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只有偶尔翻阅拍卖图录时微动的手指,泄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竞拍过程波澜起伏。前面的作品陆续落槌,有惊喜,有遗憾。当那幅压轴巨作被隆重推上展台时,全场瞬间安静下来,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起拍价不菲,竞价迅速白热化。几个国际电话委托和现场的重要藏家轮番举牌,价格一路飙升,很快突破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江郁始终没有回头,但贺凛能看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微微泛白。
竞争逐渐集中在两位藏家之间,一位是海外背景深厚的基金代表,另一位则是国内以眼光毒辣、出手凶猛著称的私人收藏大鳄。价格仍在攀升,每一次加价都引来一阵低低的惊呼。
就在价格达到一个天文数字,拍卖师重复着最后一次报价,槌子即将落下的瞬间——
“再加五百万。”
一个平静而清晰的声音,从大厅后排响起。
全场愕然,目光齐刷刷地转向声音来源。聚光灯甚至下意识地扫了过去,照亮了贺凛没什么表情的侧脸。
是贺凛。他举着号牌,姿态从容,仿佛刚才报出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
前排的江郁,背影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没有回头,但贺凛能感觉到,那道熟悉的、冰冷的视线,似乎穿透了人群,落在了自己身上。
那位私人收藏大鳄显然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而且是贺凛这样背景的人物。他皱紧眉头,犹豫了片刻,最终在拍卖师再次催促下,摇了摇头,放弃了。
槌音落定,清脆响亮,在整个拍卖厅回荡。
掌声响起,却带着几分复杂的意味。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贺凛身上,充满了惊讶、揣测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贺凛却只是平静地放下号牌,仿佛刚才一掷千金的不是自己。
他没有去看江郁,也没有理会周遭的视线,只是微微侧头,对身旁的特助低声交代了几句。特助点头,迅速起身去办理后续手续。
拍卖会结束,人群开始骚动着退场。贺凛依旧坐在原地,没有动。他看到江郁站起身,和几位上前道贺的人简短寒暄,神情淡漠,看不出喜怒。然后,江郁转过身,目光穿过逐渐稀疏的人群,精准地落在了贺凛身上。
那眼神,不再是之前的平静、审视或一丝微弱的松动,而是带着一种冰冷的、几乎可以称之为愤怒的锐利。
贺凛的心沉了一下,但并没有意外。他迎着那道目光,没有躲闪。
江郁没有走过来,也没有说话。他只是隔着一段距离,用那种冰冷的眼神看了贺凛几秒钟,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随着人流离开了拍卖厅。
贺凛独自坐在空旷起来的大厅里,昂贵的吊灯光线落在他身上,却照不暖他周身的冷意。他预料到这个结果。用这种粗暴的、资本碾压的方式“帮”他,无疑是踩到了江郁最敏感的雷区。这甚至可能将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的那点微弱的、脆弱的联系,彻底粉碎。
但他还是做了。
不是因为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他查过那位最终放弃的私人收藏大鳄的背景,其名下艺术基金的投资风格激进且短期,与江郁坚持的长期、深度代理艺术家的理念背道而驰。如果画作落入其手,很可能会被资本快速运作、炒作,甚至影响艺术家未来的创作路径。而那个海外基金,虽实力雄厚,但其地缘政治背景复杂,近期国际艺术物流和展览合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
相比之下,由他拍下,虽然方式拙劣且引人反感,但至少,他可以保证这幅画不会沦为短期套利的工具,不会影响艺术家与画廊的长期计划。他可以将其作为非卖品收藏,或者在未来合适的时机,以更符合江郁意愿的方式处理。
他知道江郁会愤怒。
他知道这会让一切回到冰点。
但他宁愿承受这愤怒,也不愿看到江郁的心血,因为资本的短期逐利而偏离轨道。
这是一种笨拙的、自以为是的保护,也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赌江郁在愤怒之后,或许……总有一天,能明白他这愚蠢举动背后,那一点见不得光的、小心翼翼的初衷。
贺凛缓缓站起身,走出拍卖厅。外面不知何时又下起了雨夹雪,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刺骨的寒。
他坐进车里,没有立刻让司机开车。他拿出手机,点开那个依旧一片空白的聊天界面。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悬停良久,最终,还是没有落下任何一个字。
任何解释,在此刻,都是苍白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