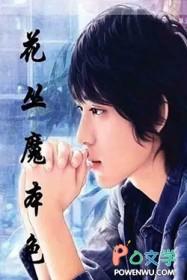紫夜小说>承爵是什么意思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江先生的事情,我们有所耳闻。秦经理那边,可能是沟通上有些误会,我会和她了解一下情况。请您放心,集团对这个艺术项目是非常重视和支持的。”张秘书的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意思已经传达得很清楚。
挂断电话后不到半小时,秦女士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对之前的“沟通不畅”表示歉意,还对江郁提出的几个核心方案表示了高度认可,后续的推进瞬间变得顺畅无比。
问题解决了。兵不血刃。
江郁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心里却没有丝毫轻松。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沉甸甸地压着他。
他厌恶这种依靠别人力量解决问题的感觉,尤其厌恶这力量来自贺凛。这让他觉得自己依旧无能,依旧被困在某种无形的藩篱里。
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否认,贺凛提供的帮助,精准、高效,且最大限度地保全了他的尊严和主导权。他没有出面,没有施舍,只是在他快要被淤泥淹没时,默不作声地递过来一根结实的树枝。
这种沉默的守护,比以往任何轰轰烈烈的“补偿”都更让江郁感到……无所适从。
他烦躁地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目光无意间扫过书架,落在那一排贺凛之前送来的艺术书籍上。他鬼使神差地抽出一本,翻开。
书页间,夹着一枚素净的书签。他拿起书签,背面用极细的笔,写着一行小字,是某种艺术评论的摘抄,关于“破碎与重构”的美学探讨。字迹挺拔有力,是贺凛的笔迹。
江郁的手指摩挲着那行小字,冰凉的纸片仿佛带着一丝残留的温度。
他忽然想起,贺凛似乎很久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周慕白”这个名字了。也没有再试图解释过去,或者追问未来。
他只是在那里。
在他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地方。
用一种他无法拒绝、也无法定义的方式,存在着。
江郁闭上眼,将书签紧紧攥在手心,棱角硌得掌心生疼。
他发现自己开始看不透贺凛了。
也或许,他从未真正看透过。
那个曾经只会用强权和无知伤害他的男人,似乎真的在学着用另一种方式,笨拙地、沉默地,靠近他。
而他自己筑起的那道冰墙,在日复一日的无声侵蚀下,是不是……也开始有了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松动?
窗外,夜色渐浓。
城市的光海无声流淌。
江郁站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却感觉自己站在一片茫茫的迷雾中央。
前路未知,退路已断。
而那个他一直试图推开的人,却仿佛成了这迷雾中,唯一隐约可见的、沉默的坐标。
久久未散
酒店艺术项目的风波,如同一块被投入深潭的石头,沉下去,便再无声息。秦女士那边变得异常配合,项目推进顺畅得不可思议。画廊上下都松了口气,只有江郁,心头那份滞涩感,久久未散。
他不再试图去剖析那条短信背后的动机,也不再深究贺凛这种“隐形”守护的边界在哪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用一件接一件的策展、一笔接一笔的交易,填满日程表的每一个空格。他重新变回了那个在艺术圈里游刃有余、冷静自持的江老板,仿佛前段时日那个在医院里苍白脆弱、在公寓里沉默用餐的人,只是一场幻觉。
只是,偶尔在深夜离开画廊,独自驾车穿过空旷的街道时,他会下意识地瞥一眼后视镜。或者,在某个需要应酬的场合,面对难缠的合作方,脑海里会不受控制地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是贺凛,会如何处理?
这念头往往刚一冒头,就被他强行摁灭。他厌恶这种不受控的联想,更厌恶因此而在心底泛起的、那一丝微弱的、类似于依赖的情绪。
贺凛依旧没有出现。他像彻底从江郁的日常生活中蒸发了一般,只留下无处不在的、被妥善安排好的便利。画廊需要拓展海外渠道,便有顶尖的咨询公司主动接洽;江郁看中某位新兴艺术家,总能在拍卖会上以合理的价格顺利拿下;甚至连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都“恰好”引进了他偏爱的一款稀有咖啡豆。
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若不是江郁心知肚明,几乎要以为是自己时来运转。
时间滑入深秋。城市被金黄的银杏和火红的枫叶装点,空气里多了几分凛冽的清爽。
江郁接到一个国际双年展的策展邀请,意义重大,他需要亲自飞往欧洲进行前期考察和洽谈。行程定在下周。
出发前三天,他正在画廊核对最后的行程细节,助理内线电话进来,语气有些古怪:“江总,前台有一位……贺先生的特助,说有东西要亲自交给您。”
江郁握着话筒的手指微微收紧。“让他进来。”
特助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个看起来十分古旧的紫檀木长盒,神色恭敬:“江先生,贺总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江郁看着那个木盒,没有接:“这是什么?”
“贺总说,是物归原主。”特助将木盒轻轻放在办公桌上,便躬身退了出去,没有多余的一句话。
办公室里只剩下江郁一人。他盯着那个散发着淡淡木香的盒子,良久,才伸出手,打开了盒盖。
里面铺着深蓝色的丝绒衬垫,衬垫上,静静躺着一卷泛黄的宣纸画轴。
江郁的心跳漏了一拍。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画轴,缓缓展开。
墨色苍润,笔意遒劲,山水氤氲间,自有一股磅礴之气。右下角的钤印和题跋,赫然是那位他已故恩师——国内画坛泰斗林老先生早年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