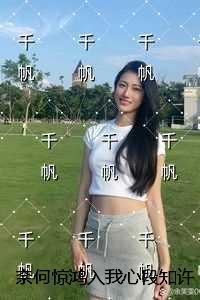紫夜小说>太子逃跑 > 4050(第12页)
4050(第12页)
药膏冰凉,谢念下意识瑟缩了下,谢告禅摁住他的小腿,不让他乱动弹。
谢告禅力道极轻,最开始上药那点凉意过了之后,就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动作了,浓重的药味再次弥漫开来,谢念眉头微蹙,不过很快就强制让自己放松下来。
“……只是觉得太麻烦皇兄了。”谢念声音很小。
谢告禅一开始没说话。
他手上动作没停,过了会儿才开口:“不算麻烦。你小时候也摔过,从玉寒池那里,比现在严重。”
嗯?
谢念回忆了下,对这段记忆毫无印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落水之前,”谢告禅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似的,头也未抬,语气淡淡,“七八岁的小不点儿,居然敢一个人往那偏僻的地方跑……真是一点没变。”
谢告禅话中有话,谢念耳根微红,声音显得更小:“……我不记得了。”
他一直以为和谢告禅熟稔起来是在落水之后,没想过在此之前还有过接触。
“皇兄怎么发现的?”谢念又问道。
“当时你身边没人跟着,又走在池边,我便唤翁子实将你带过来。”
“你当然不从。”
“然后我亲自将你带到太医院,”谢告禅面无表情,“你又哭又闹,不肯让太医靠近,我只能把你带回东宫,亲自上药。”
谢念默默将头埋下去,以此掩盖自己越来越红的双耳。
然而谢告禅并未有要停下的意思。
“你当时还未恢复皇子身份,非说若是有了肌肤之亲,就只能嫁给我,所以誓死不从,喊得连太傅都来问我发生了什么。”
谢念闻言,有些震惊地抬头,眼眸微微睁大,张了张嘴,一时间哑然。
“我以前这么,这么……”
这么蛮不讲理吗?
“骗你作甚?”谢告禅语气淡淡。
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谢告禅那时候也是头次遇见敢在他面前这么撒泼打野的,震撼到连太傅问他时都回得支支吾吾。
太头疼了。
谢告禅温声哄劝,谢念却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哭喊着要回到自己的寝殿。谢告禅无法,只能又拉着谢念的手,走过大半个皇宫,回到谢念那破破烂烂又寒酸的寝殿里。
说是寝殿,其实四处漏风,连个能落脚的地都没有,谢告禅一走进去,甚至还看到了从角落逃窜出去的野耗子。
生存环境可谓相当恶劣,可谢念回到寝殿后反而安静下来,和谢告禅掰扯半天,最后被读书更多的谢告禅绕了回去,乖乖在眼前系上白纱——看不到,那就等于没有接触。
直至谢告禅将层层叠叠的长裙卷起一点后,才明白谢念为什么不让旁人碰。
脚上布满冻疮,溃烂红肿,他抬起头,才发现谢念一直好好隐藏在袖子里的手上也长了好几个,大面积连在一起,隐隐还有脓血流出。
谢告禅帮他上好药后,看了一会儿才离开。后面几天他一如往常给谢念上药,又让翁子实将份例里的银丝炭拨出来一部分,接连过了好几日,看见谢念手上脚上的冻疮渐渐消下去,他才放心下来。
念及此处,他又扫了眼谢念搅在一起的细长手指。
好在没有留疤。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以前这么难缠……”谢念试图辩解。
虽然自落水后九岁前的记忆变得一片空白,但谢念实在想象不出,自己以前撒泼打滚是什么样子,光是听谢告禅这么描述,都觉得脸上烧得慌。
他还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呢。
谢告禅语气没什么变化:“现在也一样。”
谢念一怔,片刻后脸变得更加滚烫。
像是打开了记忆的旧匣子,从前的回忆争先恐后般朝他涌了过来,像是片片肆意飞舞的雪花,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
仔细想想,他以前好像也做过不少类似的事情。
白日里缠着谢告禅教他写字,晚上还要贴着谢告禅才肯睡,平日里就像个小跟屁虫一样,天天跟在谢告禅身后喊“太子哥哥”……
好丢脸。
谢念深吸一口气,试图将脸上的燥意也一并压下去。
“好了。”谢告禅松开手,起身。
他走到铜盆前,细细将指缝里残留的白色药膏洗净,确认那种浓郁又古怪的药味消散了之后,才重新回到床榻前。
这间客栈的床榻十分狭窄,将将能躺下两个人,想要翻身,或者略微动作,都很可能会和另一个人碰到一处。
等他转过来时,谢念已经将自己缩在角落里。他本就纤瘦,占不了多大地方,面对如此窘迫的长度,竟是硬生生给谢告禅留出大半空余。
谢告禅垂眸,没说话。
烛火适时熄了。
厢房陷入一片漆黑。在夜色当中,平常听不见的声音好像都被无限放大,衣料摩挲的声响在谢念耳边响起,而后身侧床榻微微下陷,熟悉的雪松气息再次笼罩了他,那点古怪的药味好像也被压制住,几乎闻不到了。
谢念紧绷的脊背放松下来,几不可闻地舒了口气。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奈何惊鸿入我心段知许江疏桐:全文+结局+番外段知许江疏桐
- 段知许心头一震,猛地转过头去。那一瞬间,他几乎以为那是江疏桐。可当他看清来人时,才发现是段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