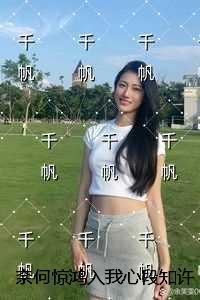紫夜小说>藏高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 > 第41章 嫌隙 别碰我(第2页)
第41章 嫌隙 别碰我(第2页)
“属下正要说这件事,此次行刺的刺客,原属幽州大司马麾下,据传,是一名幕僚,名为贺楚筠,颇受其宠幸。”萧驰节也曾是斥候出身,如今升了官丶跟着打了许多场仗,探查消息一事也仍旧多是由他负责,“至于婉儿姑娘提到的那名刺客,外貌上也确实是和贺楚筠一致,幽州大司马麾下,仅这一人。”
江煦不置可否,淡淡道:“皇都那边,想必也少不了幽州的人插手。”
洛阳为古都,粮田丰茂,商业繁华,士人多居于此,文化气息浓厚,同样也很适宜居住,经年累月下,勋贵不胜其数。
故而,其中的腐败同样稀疏平常。
南元朝堂算是由国舅宁鸿把持朝政,素来推崇正统嫡出,庇护着小皇帝,可。。。。。。吏部尚书裴晟则不然。先前的买官费没收到手,裴晟又与毛懋艟交好,北方的暗线还被他一锅端了,这人不可能全然没有t动作。
江煦回想着那刺客的模样,须臾,又再度执笔,这回,端正的楷体现于纸面,待墨迹稍干,便将此封信笺递给萧驰节。
收回心思道:“这信你亲自去送,给当今圣上。”更是给国舅。
“不出意外。。。。。。若他们那边肯首,不日,定会派使者前来戍边。”
届时,方可顺藤摸瓜,一一将其斩下。
*
临近立冬,廊下时有冷风刮过,一株新梅斜伸入窗,枝头将绽未绽的花苞裹着薄冰,在晨雾中随风浮动,泛起一阵琥珀色调的光晕。
画澜熄灭烛火,旋即候在一边,只等着莳婉起身梳洗,可好半晌,还不见起,室内反倒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熟悉且令人揪心。
她掀开帘子一瞧,果不其然发现莳婉面色绯红,泪光点点,鬓蝉雕落柳眉颦,俨然已是又病了,画澜心下一惊,见画蕙端着早膳回来,忙唤她守着,脚下生风跑去正院。
待她赶去,江煦恰好习武归来,沐浴更衣完,正与景殷丶景彦商议事宜,乍然听闻婉儿病了,他神情微怔,但转瞬便像是想到什麽,只嘱咐了两句,派军医去瞧。
直至午後,莳婉的头都还是昏沉沉的,两副药下肚,整个人更是昏昏欲睡,房门外,似乎传来几道低声的交谈,像是在讨论她的病情。
她凝神去听,晕乎乎的,却是什麽也没听清。
忽地,门扉一动,莳婉心下狂跳,勉强集中了几分精神。
一道修长身影立于塌边,覆下大半的阴影,挡着窗棂外零零碎碎的光。
江煦的嗓音透过重重帐幔的阻隔传来,很轻,像是不可置信,夹杂着一股明显的质疑,“病了?”
莳婉强撑着精神,睁开眼,眼前一片模糊,好几息才渐渐显出男人熟悉的轮廓,嗓子发疼,脸色发烫,不必细想,她此刻定然极为狼狈,边想着,她下意识轻阖着眼,不看他。
然,这幅因身体虚弱而伏低做小的可怜模样却是极大地取悦了江煦,他温声道:“看来确实是身子不适,瞧着。。。。。。倒是乖巧了许多。”
她只着一身素色寝衣,身量纤纤,弱不禁风的姿态,惹得他心下一动,两人昨日才不欢而散,若是其他事情,江煦定然不会这般和颜悦色。
莳婉有些厌恶这道赤裸裸的目光,卯足力气半侧着身子,整个人背对着他。
见状,江煦满心的怒火消散一二,“军医说你这病来的蹊跷,是心病。”
可见婉儿心底,还是不像她面上表现得那般镇定自若的。
回神,他温和道:“若是你与其他人有旧,现在说出事情,也算尚可。”男人顺势坐在床榻边,边说着,就要去探莳婉的额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谁知话音刚落,宽大的手掌刚一伸出,便被一道苍白的手背打掉,江煦一愣,手掌悬于半空,擡眸看去。
婉儿似乎离得更远了些,嗓音细弱蚊蝇,裹着药香飘散,传入耳畔。
“别碰我。”
-----------------------
作者有话说:“鬓蝉雕落柳眉颦”出自《太真卧病图》,作者是宋朝的胡仲弓。
嗓音裹着药味的馀韵,显出几分决绝,最终消弭在一声压抑的咳喘里。
“咳咳。。。。。。”
莳婉强忍住喉间的痒意,紧抿着唇,隐隐察觉到身後的视线,身子不自觉再度往里靠拢,试图避开。
青纱帐低垂,鎏金香炉轻吐着袅袅青烟,另一扇紫檀屏风将卧房隔成内外两重天地,江煦侧坐床榻,面色如常,神色依旧是淡淡的,但这样平静,却莫名叫旁人心下悚然万分。
须臾,莳婉迷迷糊糊听到帐幔外传来一道吩咐,几不可闻的脚步声响起,室内一时落针可闻。
她这才恍然,惊觉有些不对,擡眼,倏然撞上江煦黑黝黝的眼神,他没开口,只冷冷笑了下,幽幽重复了遍她方才的话语,“别碰你?”
他想到了婉儿先前的那些话语,又见她知晓那些被罚之人的下场之後还敢如此,一时眼底神色更冷。
这句话仿佛触碰到某种隐秘的机关,直叫莳婉有些不好的预感,她索性不说话,只兀自垂眸,盯着床褥的一角发怔。
江煦的视线恍如毒蛇,轻柔但不容忽视,微凉的触感一下又一下盘绕脚心,而後是脚踝丶小腿,沿着往上,愈发寒凉。
室内炭火充足,她却生生漫出几丝冷汗,贴着发梢鬓角,混合着因服药安睡而生出的热意,两者交替,好不磨人。
他定定地盯了她片刻,忽地起身往一侧的窗案去,取了一摞纸张一样的东西,莳婉心下顿感不妙,强撑着呵斥道:“你做什麽?”
但她如今太过虚弱,方才那一下便已经耗费掉大半力气,如今吐出的话语反倒像是轻声的问询,少了几分咄咄逼人的劲儿。
江煦不为所动,只将那些东西尽数放置在床榻边的梳妆台上。
梳妆台隐在帐幔阴影里,上头镶嵌着的玳瑁彩贝熠熠生辉,泛着莹润的光泽,江煦将那摞纸张一样的东西放了上去,莳婉这才看清楚,是银票。
不止是银票。
还有金锭和许多碎银。
莳婉微微发怔,坐起身背靠着床的一侧,望向梳妆台那侧,见江煦气定神闲,心里不安之感更重几分,“江。。。。。。你做什麽?”
江煦听见莳婉再度想要唤他的名讳,面上讽刺更甚,“从前的桩桩件件,本王似乎。。。。。。还未同你细细算过吧?”
“你是何意。。。。。。?”莳婉猛然生出些惊惧之前,凝神望他。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奈何惊鸿入我心段知许江疏桐:全文+结局+番外段知许江疏桐
- 段知许心头一震,猛地转过头去。那一瞬间,他几乎以为那是江疏桐。可当他看清来人时,才发现是段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