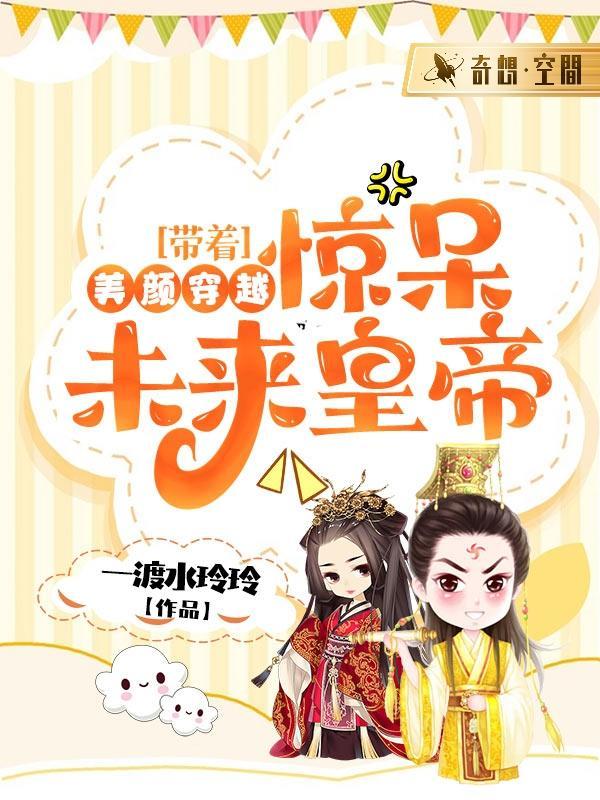紫夜小说>钻狗洞后爱上小奶狗 > 第38章 纸外之人一 呐给你的(第2页)
第38章 纸外之人一 呐给你的(第2页)
裴青寂低下头,指尖在掌心里缓缓收紧,指节被风吹得发白。
忽然,胳膊上被轻轻碰了碰。
“PlanB,你准备好了吗?”
林序南的语气就像在问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轻巧到几乎要把裴青寂从那段冷硬的回忆里,生生拉了出来。
“放心。”
裴青寂转过头笑了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辛苦了辛苦了!”方砚笑嘻嘻地拍了拍裴青寂的肩膀,动作看起来熟稔又亲切。
随後,他笑着转过头,看向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声音立刻提高了几分,带着官方式的热情与骄傲,“这就是我们课题组的裴青寂裴博士,这次的项目如果没有他,恐怕还真没办法这麽顺利完成。”
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亮起来,镜头全都对准了裴青寂。
裴青寂垂下眼睫,视线透过镜头,看着那些举着话筒的手和一张张带着职业微笑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这些人曾经也举着话筒喊过他的名字,曾将他捧上过高位,也曾毫不留情地将他推下深渊。
可现在,他必须让他们再次看见自己。
必须。
采访很快开始。
镜头里的方砚,西装笔挺,精神矍铄,声音铿锵有力,句句不离“蛋白凝胶技术的开创性”丶“可大规模推广的産业价值”,还有“材料科学与古籍修复的跨学科创新”,每个词都像瞄准目标的子弹,直击“科研成果转化”与“国家项目”的靶心。
裴青寂站在他身後,目光平静,神色淡淡,唯有指尖轻轻敲击着衣角。
“接下来,我们请到这次清溪市檐雨书院古籍抢救修复项目中,负责具体古籍修复与材料应用结合的裴青寂博士,来谈谈他对这次救灾修复项目的理解。”
灯光追过去,摄像机缓缓拉近,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到他身上。
裴青寂擡起头,看着镜头,薄唇轻啓,声音不疾不徐。
“这次项目,从材料研发到灾後应急应用,当然证明了我们蛋白凝胶在纸质文物纤维强化方面的优势。”
他顿了顿,眼神不动声色地扫过那个安静坐在後面的林序南。
林序南正撑着下巴,目光专注地看着他,眼尾微微上挑。
裴青寂的声音轻了半分,低沉却更加清晰。
“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古籍被救下来了。”
他擡手点了一下鼠标,身後的PPT上清晰地呈现了一张古籍的图片,封面带着浅浅的水渍痕迹。
“比如这本明代的《吴门岁时杂记》。”
“它记录了当年苏州的岁时节令丶民间风俗丶饮食茶点丶四季物産。”
“它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们,春天会在玄妙观前看百戏,夏日喝梅花酒,七夕去虎丘拜织女,冬天就吃青菜萝卜豆腐汤。”
“这里面写的不仅仅是‘历史’,不是被定格在博物馆橱窗里用玻璃罩隔绝呼吸的标本,而是当时每一个活着的人,真实呼吸过的空气,路过的街巷,尝过的味道,和爱过的人。”
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原本嘈杂的采访现场,突然安静了下来。
“这就是我想做这件事的原因。”
“不是因为它可以证明我的技术有多厉害,也不是因为它能带来多少科研经费。”
“而是它值得被救。”
最後一句话落下,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
那些原本举着话筒丶正准备继续追问下一个“科研亮点”的记者们,一时间都没能开口。
聚光灯依旧亮着,落在裴青寂脸上,也映在每个人的眼底。
空气似乎凝滞了片刻。
直到方砚轻轻咳了一声,笑着接过了话筒,“感谢裴博士的分享。他对文物修复的理解,正是我们这次项目最大的意义所在。”
采访结束後,记者们热烈地和方砚握手,连声说“完美丶顺利丶感谢配合”。
方砚笑着,心情显然极好,转头看向裴青寂,但是他的眼神却透着几分打量。
“青寂,你後面那段,感情不错,就是少了点科研成果的拔高,如果再多强调一下蛋白凝胶的创新点和市场推广价值,会更好。但问题不大,回去好好休息吧。”
裴青寂点了点头,淡淡应着,没有再解释什麽。
“呐!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