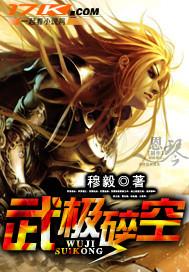紫夜小说>逃婚碰到爱 > 第11章(第2页)
第11章(第2页)
自从有过那先前那一遭,豆芽也不怕了叶昭,回道:“石头。”
唤作“石头”的,正是那日接了叶昭烧饼的另外一个哑巴男孩。闻言,张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朝叶昭比划了几下。
叶昭扭过头问:“他在说什麽?”
豆芽答道:“他说谢谢恩公您。”
“道谢归道谢,有些事还是要说在前头。先前你们做了偷窃之事也罢,此後能答应我好好好走正道吗?”叶昭正色道,说完又加了句,“我也只是个小小侍卫。陈家是大户人家,要是出了什麽事,不单单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的饭碗也保不住了。”
一大一小姐弟连忙点点头,一幅信誓旦旦的样子。
等到了医馆里头,叶昭便见着正打算坐诊的陈禾。
她清清喉咙,对陈禾道:“陈叔,这些孩子就麻烦你了。”
陈禾捋捋胡子,上上下下打量叶昭一眼,道:“沈公子早与我说过,先前施粥救人之事,早就听闻公子。我既答应了,此事便不在话下。”
叶昭点点头,又说上几分感激的客套话,想着闲来无事,不如在这医馆中帮衬会子,等到下午时分再去粥棚那边帮衬。
***
城外施粥之事,一连便是五日。
喜的是,同济医馆乃至叶沈二人声名一时。悲的是,自从施粥的消息传开後,不知不觉中,涌向城外的流民更多了,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真要解决饥荒问题,还是得等京城运来的赈济粮才是,要不然,也得是那边传令过来,当地才好开仓放粮。
这晚,忙活了一个白天的叶昭返回陈宅,进门前忽地瞥见对家院门外,一个小厮正往门口泼水,泼完後猛地一声关上门。
进门时,她恰巧见得院中负手而立的曹九,问了声“好”後,不免得疑惑问道:“曹管家,在下有一事请教。方才我在门口,看见对门的小厮往门口泼水。难道……这是本地的什麽风俗?”
“那倒不是。”曹九耐心解释道,“那阵子公子还没进城,城外闹了灾,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便随着人流入城,晚上无处可去就睡在人家宅院门口,在我们这样的高门大户门口是常有的事,就有人想出泼水的法子,地上湿了自然就没人睡了。正因如此,後来知县才下了城门令,严禁难民入城。虽说现在城内流民少了,但是这习惯还是留下了,算是前车之鉴罢。”
联想到刚入城时两个守卫所言,叶昭心下一动,想道:“不允许酉时以後入城,怕不是担心难民夜深人静偷偷溜进城?这城门令,虽说是护住城内的安稳,但城外就这样压根不管麽?知县做的,未免还是狭隘了些。”
正思忖之间,瞧见从屋门口出来的墨竹,手中还端着个托盘,便告别管家向前走去。
走近後才发现,原来托盘上端着的是个白瓷碗,散发着淡淡的苦味。
叶昭出声唤住他道:“这药是怎麽回事?你家公子生病了?”
“和你有什麽关系?”墨竹低头嘀咕两声,语气不冷不热,说完後径直离开了,只馀下叶昭一人在风中凌乱。
叶昭直觉不对,虽说这小书童有几分脾气,但这幅样子更像是被踩到痛处後的避而不谈。忙推门而入,只见姓沈的端坐桌旁,正在细细抿茶,面色还算滋润,倒也未看见有什麽异样。不过,她还是不由得说几句关照的话:“刚才在门外,看到墨竹端的药碗了。你……的身体怎麽样?”
“身体如何?”沈清淮擡眼看她,片刻後垂眼,神色格外落寞,“我确实自幼体弱多病,身患不治之症。”
叶昭呼吸一滞,没想到他这般回答,还以为先前在地窖里头所说的“体软多病”之言,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上前当出头鸟罢了。如此这一问,怕不是真的触碰到了对方的伤心事。不是说这江南陈家是什麽杏林世家麽,难道也没得法子?
她不由得握紧了身侧衣角。
就在这时,沈清淮放下手中茶水,再擡眼时方才的脆弱神色荡然无存,语气轻飘飘的:“骗你的。”
顿了顿,又道:“体寒而已,起码还能活上个十年八年。”
叶昭:“……”
这人说的话,到底还有几分可信?
叶昭便收了关照心思,转而说起正事:“我想与你说说施粥一事。我在想,既然米价优惠,何不索性多买些囤粮?还有,听说好几个地方乡绅有意参与施粥,有意积德行善。不如索性一同去米行谈谈价钱,在城外以及广德寺等寺庙口组织施粥。”
沈清淮:“真要如此,也是个法子。不过还得从长计议。”
不多时,门外又传来脚步声阵阵。陈禾推门而入,面色格外沉重。
见状,沈清淮问道:“陈世伯,可是出了什麽事?”
陈禾眉宇紧锁,长叹一口气:“今日傍晚,医馆来了好几位闹肚子的客人,说是喝过我们分发的米粥。”
沈清淮立刻反应过来:“他们怀疑是我们故意用劣米去施粥,好让百姓闹肚子,再反过来为医馆招揽生意?”
叶昭当下就急了,接话道:“怎麽可能?米……米是从福源米行买的。不行,那姓荀的掌柜住哪儿?我今晚就得去找他问个清楚!”
陈禾望向两人,回道:“这正是我要说的。就在今晚,荀良掌柜死了。”
![今天开始当天使[西幻]+番外](/img/2842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