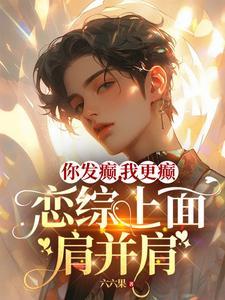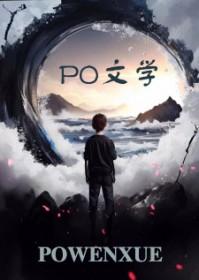紫夜小说>穿越七零大杂院当富婆 > 第37章 技艺展示 木兰花开艳四方(第1页)
第37章 技艺展示 木兰花开艳四方(第1页)
林建华站在裁缝间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汤,没急着进去。他看见秀芬正低头在纸上写什么,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桌上摊着几张布样,深蓝底白花的那块被压在本子下面,只露出一角。
他推开门,热气跟着人一起涌进来。“还没歇?”
“快了。”秀芬头也没抬,“把明天要摆的几件衣服再核一遍。”
林建华把碗放在桌角,顺手拿起那块布料看了看:“就这件?”
“嗯。领口盘扣我改了三回,才做成木兰花苞的样子。”她终于抬头,眼里有光,“我想好了,叫它‘木兰初绽’。”
林建华笑了下:“名字倒讲究。”
“不光是名字。”她把笔放下,“这一针一线,人家都看在眼里。咱们清白做事,也得让人看得明白。”
第二天一早,赵大妈拎着个竹篮进了院子,里面装着刚蒸好的两屉菜包子。“先垫垫肚子!”她把篮子往秀芬手里一塞,“待会儿人多了,你可没空吃饭。”
孙寡妇也来了,怀里抱着一叠剪好的红纸花,边沿整齐,花瓣舒展。“贴墙上还是门上?”她问。
“都行。”秀芬接过,“你费心了。”
吴婶从院门外探了个头,见人都在忙,迟疑了一下才走近,把手里的红绸布往窗台上一放:“这个……能当挂饰用。”说完转身就走,脚步比来时轻快些。
钱婶到得晚些,穿着洗得白的灰呢外套,手里还拿着一本旧书。她没多说话,只问了一句:“需要我帮忙念个开场词吗?”
秀芬愣了下,随即点头:“您肯来,就是撑场面了。”
下午一点刚过,裁缝间的门就被推开了。王专员穿着藏蓝列宁装,胸前别着妇联徽章,身后跟着两个街道干事。她环顾一圈,目光落在墙边挂着的几件衣服上,点了点头:“准备得挺周全。”
“您能来,我心里踏实多了。”秀芬迎上去。
“不是我来不来的问题。”王专员声音不高,“是你这一步走得对。手艺要传下去,先得站稳脚跟。”
两点整,人差不多到齐了。街坊们挤在门口,有的踮脚往里瞧。林建华搬了两张长条凳摆在屋中央,又把电灯拉得更亮些。秀芬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第一件展品——一件绣着小梅花的儿童围兜。
“这是我给乐乐做的。”她举起围兜,“针脚密一点,孩子穿得久。布是旧衬衫改的,线是拆了毛衣重新捻的。不值几个钱,但用心了。”
底下有人笑出声。赵大妈大声说:“我家孙子现在还穿着她改的裤子呢,屁股那儿加了宽边,蹲着不扯缝!”
秀芬笑了笑,接着拿出第二件——男式棉袄,内衬缝了一圈细布条。“这个防滑,穿久了肩带不会往下溜。”她说,“是我给老郑爷做的。”
郑老爷子坐在角落的小凳上,拄着拐,没吭声,只是把手伸进袖口摸了摸,轻轻点了下头。
然后,她取下了那件旗袍。
深蓝底,白色木兰花顺着右襟一路斜向上开去,领口的盘扣真的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屋里一下子静了。
“这件,我想了很久。”秀芬轻声说,“以前总觉得好衣服是富贵人穿的,我们这种人家,能遮体就行。可后来我想通了——女人不管日子多紧巴,也该有让自己高兴的一刻。”
她回头看向王霞:“你愿意试试吗?”
王霞愣住:“我?”
“你身材正好。”秀芬已经把旗袍递过去,“换上吧,让大家看看。”
王霞咬了下嘴唇,接过衣服进了里屋。几分钟后,门帘一掀,她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旗袍贴身却不勒,腰线收得恰到好处,木兰花从肩头延伸至裙摆,像是随风轻轻摇曳。她缓缓转了个身,布料出细微的摩擦声。
没人说话。
然后,掌声响了起来。先是赵大妈拍手,接着是周建国笑着鼓掌,连钱婶都微微颔。吴婶站在人群后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刚才送来的红绸布边缘。
秀芬走到王霞面前,帮她理了理肩线:“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