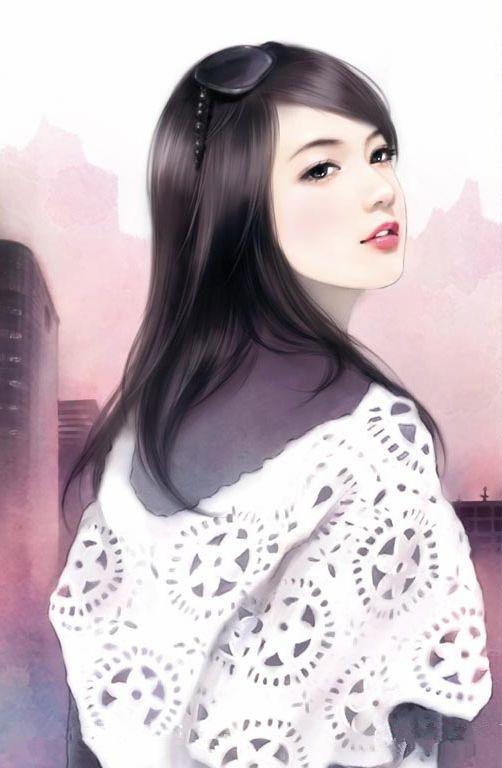紫夜小说>黑山夜话by迟行之好看吗 > 第35章 破云(第3页)
第35章 破云(第3页)
我喊回去。
“那不然呢?”
他说。
我他妈的真的服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屁股下面的马根本没有马鞍,我真的被颠得感觉骨头都在颤抖。而且我们原来的马是那种枣红色的,这匹马是白的,也根本不是原来的马。
没有马鞍,也没有脚蹬,这他妈的是匹野马。
我真的这辈子就没想到过自己会骑在野马上奔腾,这匹马完全是在全速向前奔跑,我屁股的那块的骨头不停地撞上马背,疼得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金毛完全没有被这种小问题影响。他心情很好,左手抓着缰绳——就完全是一条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麻绳,被他打结套马嘴上,另外一只手抛了一条粗麻绳到我怀里。
“套上,”他说,“把我们俩绑一块。”
我完全不知道他干嘛,但他说了,我哪敢不做。我用力把绳子抛高,前两次落下的时候打到了金毛的头,金毛爆了一句粗口。
我身家性命押在了他身上,他现在让我喊他亲爹我都不敢不喊,只能忍气吞声。好在第三次抛起来的时候正确落到了他身後,我马上拉进绳子,就要捆在自己腰上。
但我一拉绳子就感觉出不对劲来了。
这根麻绳很长,勒紧的时候应该有很多宽馀,并且勒到人和勒到其他手感是不一样的。我拽绳子的时候感觉绑到的东西软绵绵的,没有实在的手感,像是勒到了什麽包裹之类的东西,不太受力。
我虽然不知道为什麽要绑,但我还是怕那个绳子勒得不结实,就在他怀里侧身伸手,想要把绳子拽下来,然後绕过包裹,绑在他的腰上。
我拽了两次,不太能动,只能回头得更多一些。
就这麽一回头,我就看见金毛背後,有黑色的头发。
现在天已经蒙蒙亮,我绝对不会看错那种跟水草一样飘散的长发,我狠狠地眨了几次眼,那种被风吹起的头发质感非常真实,金毛的脖颈後还有一片模糊不清的阴影,像是半个侧着低头的脑袋。
都不用说猜测,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他背後贴着一个人。
“人!!!”
我撕心裂肺地惨叫,差点就松手没抓住绳子,反应过来又马上牢牢把绳子攥在掌心里。“人!!”我又喊,“你背後有人!!”
“那是鬼!”金毛语气非常轻松,几乎让我怀疑背後贴着个鬼是正常的,“所以让你绑起来!绑结实!”
“我们弄死他。”
他在我耳畔,带着难以压抑的兴奋,这样说。
他说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我真的突然觉得他很可怕。
这种可怕触及到的是本能的避险反应,在街上你看见神色异常,衣服脏乱的人你肯定不会迎上去。人类对于有精神问题的人潜意识里就会避开,这是让所有人恐惧的不稳定因素,这点我深有体会。
这一刻我意识到了或许金毛也有精神问题。人是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并去冒险的,但登上雪山与处决鬼怪完全是两个阶段。後者的危险程度无异于直接从十楼一跃而下,生还的可能性极小。
在可以选择活下去的时候,毫无意义地转头走向九死一生的死路,试图用自己一辈子只能一次的破命与那些不老不死的东西决一胜负,如此收获与付出不成正比的事情,这不是疯子是什麽?
他们这群人,好像都是这样的疯子。
我不说话了,只是去努力抓那条绳子,扯过来打结。绳子上面有点桐油,很难抓紧。我被颠得不好受力,试了好几次也只把第一个结打上。
“你还怕勒死他?”
金毛说。
“闭嘴!”
我抓麻绳都抓得手疼,又拼命拉了三次才勉强把结绑在我肚子上。那条绳子非常粗糙,需要绑得很紧才能有金毛想要的那种效果,马一上一下顶着我的胃,很快那种熟悉的反胃感泛了上来。
金毛没有减缓任何速度,眼看着天色越来越亮,层层叠叠的乌云後可以直接看见那轮新生的太阳,正在缓缓地刺破黎明前最後的黑暗。云在走动,风在啸叫,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有我攥紧绳子时发出的喘促气的声音。
隐隐约约的,我似乎听见金毛背後的那个东西在讲话。
它的声音非常沉,音节混杂着风声,几乎没有办法听清楚。我只屏息听了几句,还不知道它在说什麽,突然之间眼前就炸开了大片大片的黑斑,眼球一下子非常疼,像被什麽东西刺了一样。
我“呃”了一声,刚想要擡起一只手摸一下眼睛,突然肩膀一疼让我尖叫出声,刚想回头,眼睛的疼痛竟然又马上缓解了。
是金毛,金毛刚刚咬了我一口。
我大脑马上清醒了很多,我意识到是那个声音导致的,赶忙有意识地转移注意,攥紧手里的绳子,紧到即便是我现在死了手都没办法被掰开。
还是不甘心,既然已经逃过一劫,就总觉得不挣扎一下又是浪费。
就这样又持续了有一分钟左右,然後,太阳升起来了。
几乎只是一瞬间太阳就跃出了地平线。它的形状非常圆,是一种深深的橘红色,在爬升出来之後又慢慢变浅,直至变成耀目的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