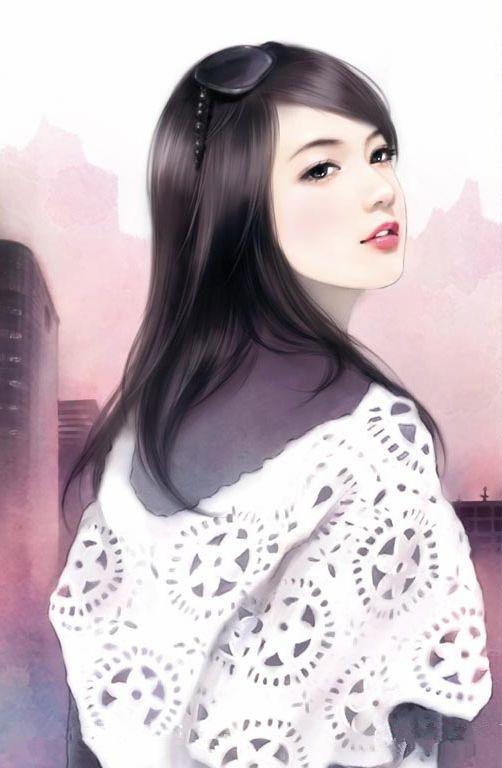紫夜小说>黑山夜话by迟行之好看吗 > 第61章 目视前方(第3页)
第61章 目视前方(第3页)
我嘴动了几下,周子末感觉到了,他把手放开,俯下身来听我讲话。
“北斗七星。”
我含糊地说。
他愣了一下,擡头看着我视线所在的方向。
过了几秒,他突然笑了。
“对!北斗七星!!”
他说,更多的笑声滚落,他贴近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我听见老陈也笑了,在这阵夹杂着草味的夜风里他们都在笑,我完全不觉得这有什麽好笑的,但最後我也笑了。
风很凉,我想到了很多事情,却好像什麽也没想。这一切都像一场梦——万幸,并不是很糟糕的一场梦。
我笑了一会,只觉得自己的体力连笑出声都不支持,只能暂停计划,急促地喘了几下。周子末用他那脏手翻我眼睛,我打了他一下。
“稳定了,”周子末说,“至少能撑到医院。”
老陈“嗯”了一声,他继续开车,我们又都安静了下来。
我真的很想提议稍微休息一会儿,但随着我的五感渐渐回归正常的一半水平,我听见了更多。
那是一种从草上擦过的,非常细碎的脚步声。在风声中不算太响,但明显和风吹过的声音不同,它在我耳旁左右闪动,像一首左右声道不停切换的歌,让人很难分辨它到底从哪开始唱起。
并且,从某一时刻开始,这种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似乎就在追着我们的车後轮子跑。
我不知道他们听见了没有,我给周子末打手势,指後面,他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正在风声中和老陈说些什麽。
他的声音不大,不知道是不是怕被汽车方向盘听见,反正我一点也听不清楚。老陈没有怎麽回答他,但我百分百确信他们在谋划着什麽。
身体上的不舒服终于被我的意志力战胜了,我决定起来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麽。我支撑着起身,周子末转过头来,不知道我要干嘛,但还是後退了一点,给我让出位置。
我探头,向後看。
周子末几乎是马上就把我的脑袋掰回来了,他用的力气有点大,但我完全愣住了,甚至没能反应过来打他一下。
我看见了。
我马上开始流鼻血,眼睛不受控制地上翻。周子末骂了一句,然後狠狠地掐了我的大腿。他瞄准的就是我身上的黑斑,手指几乎要陷进我的皮肉里,我疼得瞬间找回了一些自我。
我看见了。
我看见那座巍峨的山转身後的背影。
我们身後,是层层叠叠的黑影,像山峦一样被看不见的线描绘着。那里没有一颗星星,却有无数条向四面八方延伸开的线条,像一张纸的折痕一样,一旦産生就无法轻易抹去。
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过去,未来和现在,所有的时间,空间和引力都收束在此等庞然大物的身上,它离开,撕扯掉了罩着这片土地的那层无形的薄膜。草原从它的影子下钻出,开始重新呼吸。
而我知道那并不是它的背影,那至少它的一片还未来得及拂去的衣角,否则我绝对不可能继续在这里活着喘气。
它的衣角即将抽离,我看见了,在它的夜幕下,那些奔跑的黑影。
莽古斯,那些狼形状的怪物。
我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也不确定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追我们,还是它们也只想逃离那座山离开之後坍塌的这片天地。那些细长的,多手足的影子沉默地奔跑着,在我们身後,月光下,那些模糊的眼睛似乎在反射着银色的光。
还有其他的声音,更多的声音——不只是莽古斯。它的离开撕裂了这里的时空,我们要逃走,它们也要逃走。
那里有奇妙的哀鸣,有尸体闪烁时压落高草丛的沙沙响声。在它们之中穿梭着动物的声音,马的嘶鸣,牛的咀嚼,羊的沉吟,还有千万只手掌拍着地面的声音。
好多东西在跟着我们,我们在月下疾驰,像山火时一起奔跑的鹿,羚羊和豹子。我意识到地下的那些水泡子似乎也在跑,它隆起,消失,远处那棵巨大的树也出现,消失,再出现,那些细长的腿脚从我视线仅仅能撇到一点的地方晃过,它们都在逃。
没有什麽东西顾得上攻击别人,我们只是在逃,逃,逃,混杂在各种非人的生物中越跑越快,想要在它完全离开之前冲出这片即将坍塌的故事。
这里的秘密如同潮水般消退了,从今以後它将再也不是活着的神话。公主幡,莽古斯,灵魂,狼,还是羊,它们身上的魔法正在褪去,像一只手撕下了这个神的时代最後的篇章。
这片土地已经不再是神的土地,它回到了人的手里。它们即将退居回不可察觉的黑暗深处,从此之後神话只是故事,信仰也仅仅只是信仰。
我们见证了权柄交接之间,最後的一刻。
我仍然想看这一幕,看如此恢宏壮丽的篇章敲下最後一个音符。我们出来了,这里也不再有任何秘密。在三代人之後,可能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些遥远的过去。没有人会相信故事是真的,也没有人再会去追寻它。
但是周子末仍然扳着我的脸,不让我回头。
“目视前方,”他说,“走了。”
我看着前面,风让我视线模糊,我知道它们其实并不会就此消失,它们像冬草一样,蛰伏,蛰伏,等待下一个春天到来。
只要还有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它们就不会真正的死去。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需要担心的了。
随着汽车发动机不堪重负的轰鸣声,我们把过去抛在身後,冲向了未来,冲向了没有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