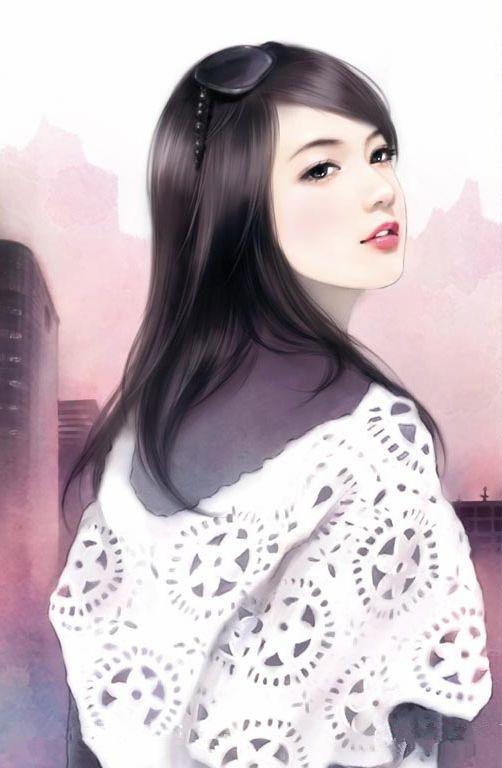紫夜小说>bella比格 > 第 28 章(第3页)
第 28 章(第3页)
途经一片嶙峋假山时,山石後传来两个太监压低的交谈声,断断续续,却字字清晰:
“……你听说没?宸妃娘娘跟前儿的人,好像对北境那几个关隘的驻军轮换挺上心的……”
“不能吧?娘娘关心这个做甚?”
“谁知道呢……许是……替哪位大人打听的?唉,不过咱们做奴才的,可不敢瞎猜,这可是掉脑袋的罪过……”
声音到此戛然而止,像是突然发现了有人靠近。
邵斯志的脚步蓦地顿住,脸上的闲适瞬间被冰寒取代。
他身後的侍卫首领反应极快,一个眼神,两名侍卫立刻如猎豹般扑向假山後方。
然而,只抓到两个面生的小太监,抖得如同筛糠,一口咬定只是在此处偷懒歇脚,并未议论什麽。
巧合?
一次或许是巧合,但这接二连三的,指向性如此明确,时机拿捏得如此精准,已然超出了巧合的范畴。
邵斯志负手立于原地,目光深沉地望着宸宫的方向,夕阳在他身後拉出长长的影子,晦暗不明。
他想起那张写着怪异文字的纸笺,想起近日宫中那些关于细作的窃窃私语,想起那些句句暗示的话语……
一股难以言喻的烦躁与猜疑,如同藤蔓,悄然缠绕上他的心头。
山雨欲来风满楼。
御书房内灯火通明,却仿佛弥漫着化不开的阴霾。
邵斯志的手指轻轻敲击着那枚做工精致的香囊,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要将其看穿。
香囊上的图腾,他认得,与边境奏报中提到的敌国标记极为相似。
而太监那些无心之语,更是精准地戳中了他最近因为边境局势而格外敏感的神经。
他没有立刻雷霆震怒,也没有传唤祁念安质问。
帝王的疑心病和多疑,让他习惯于在证据未完全确凿前,保持沉默和观察。
但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当晚,他没有去宸宫,也没有去任何其他妃嫔处,而是摆驾去了宁贵人所在的揽月阁。
他没有留宿,只是坐着喝了杯茶,询问了宁玉染几句家常,临走时,赏下了一柄质地温润,寓意吉祥的玉如意。
这个举动,如同暗流汹涌的後宫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陛下在宸妃涉嫌通敌的敏感时刻,去了与宸妃不睦的宁贵人宫中,还给了赏赐!
这其中的安抚和信号,不言而喻。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般飞遍六宫,自然也迅速传到了宸宫。
祁念安正坐在梳妆台前,由依杏伺候着卸去钗环。
她拿着玉梳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顿。
铜镜中,映出她依旧绝美的容颜,眉眼如画,唇色嫣然。
然而,那双总是流转着或慵懒丶或狡黠丶或锐利光芒的眸子,此刻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凝结起一层厚厚的冰霜,寒意凛冽。
她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缓缓地梳理着如瀑的青丝。
殿内寂静无声,只有玉梳划过发丝的细微声响,以及烛火偶尔爆开的灯花声。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依杏能感觉到,娘娘周身散发出的那种冷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刺骨。
祁念安看着镜中的自己,心底一片冷然。
她早知道会有这麽一天,只是没想到,来得这样快,这样狠辣。
香囊?关注军务?
真是好手段。
邵斯志的沉默和那份赏给宁玉染的玉如意,比任何直接的斥责都更让她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