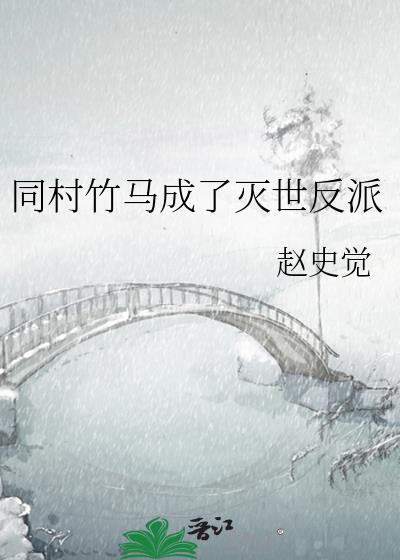紫夜小说>义父没有死 > 妄谈酒中五妄人(第3页)
妄谈酒中五妄人(第3页)
“你在强行,用三十岁的躯壳,去理解八十岁的情绪……注定,理解不了。”
她歪了歪头。
“——但是,你为什麽想要理解?一直留在三十岁,不好吗?如果,你这副皮囊是八十岁……你不会跟八十岁的情绪和解,你只会,想尽办法,回到三十岁。”
锦娘一直静静地听着。
她面前,那碗西门官特意为她准备的槐叶冷淘,还冒着丝丝凉气。
她端起茶杯,吹开浮沫,看着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
——就像眼前这五个,在各自命运中挣扎的“妄人”。
她呷了一口茶,看着那个被夏虫的“死谏”和墨陌的“天真”同时钉在原地,一脸空白的死宗高人。
她站起身,走到蹴六面前。
“道长,”她问道,“你想做什麽?”
蹴六看着她,没有回答。
“你能做什麽?”
蹴六的嘴唇动了动。
锦娘伸出手,将那根落在桌上的桃花枝捡起,递还给他。
“你该做什麽?”
蹴六看着那截桃花枝,又看了看锦娘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将那截桃花枝,重新别回发间。
苏闲语看着这一幕,看着西门官脸上的精明丶吴小二脸上的憨直丶夏虫脸上的冷静,墨陌脸上的困惑,还有蹴六脸上重新找回的疲惫和释然。
她又看了看坐回身旁的姊姊。只是问了三句话,就让一头犟狗,重新变回了“人”的姊姊。
她伸出手,握住了姊姊的手。
她笑了。
笑得像放晴的天空。
原来,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行动,都是选择。
——选择和谁知心迹,和谁托生死。
苏闲语站起身,从那盘几乎没怎麽动过的杏仁酥酪鸡里,夹起最大丶最肥美的一块,放进姊姊的碗里。
“姊姊,”她也笑了,眼角弯成了两道月牙,“吃块肉吧。你都瘦了。”
衆人酒醒,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现在……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商量一下,军机府的通缉令怎麽办?”
西门官搓着手,脸上满是宿醉方醒的疲惫与焦虑。
吴小二坐在他不远处,正和苏闲语全神贯注地比划着什麽。
“这机关手,练叼劲真快……”
两人中间的地面上,放着个透明琉璃罐,里面装着一只张牙舞爪的蝎子。
苏闲语不断用两根手指在蝎子的尾巴上“点”过,既不能被蝎子蛰到,又不能把它捏死,小脸因专注而微微出汗。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蹴六懒洋洋地回了一句,“反正,我不在上面。”
“通缉令的事,不急。”锦娘开口,“凡太尉的刀,太慢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是那种,能冒充死人的怪物。顶着我义父的脸,还能用他的金瓜槌,甚至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底细……的怪物。”
她吐出那个,让她彻夜难眠的名字:
“——无我孽。”
“他不是画皮。”锦娘续道,“画皮只能模仿外形,模仿不了‘神’,我一眼就能看透。而那个东西,它不仅有义父的记忆丶义父的功夫,甚至……连义父对我的‘慈爱’,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
“最关键的是,他被我打死前,说出的那三个字。”
锦娘的目光转向蹴六。
“解郄窾。”
“他是在主动求死。那个叫木老的妖人,写下‘王达’的名字後,便被恶咒反噬,七窍流血而亡,他死後尸体的伤损,和‘无我孽’相同。我猜,这是某种‘泄名即死’的禁制,用施术者的名字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