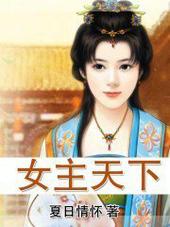紫夜小说>太子妃他只想搞钱 > 第60章 金陵苍月六 若朱庸行归入太子一(第1页)
第60章 金陵苍月六 若朱庸行归入太子一(第1页)
第60章金陵苍月(六)“若朱庸行归入太子一……
江南的夏日阴晴不定,一连数日的似火骄阳终于在某夜狂风骤雨的剥蚀下褪去些许炙热,然而这来得急去也急,至翌日已只剩下檐头寂寥的雨滴声,以及天边那枚焕然一新的太阳。待露干雾散,空气中便逐渐充斥着令人烦乱的溽闷。
晏朝外出顾不得挑时辰,一趟回来满身是汗,又黏又腻。待略作洗漱丶换过衣袍,出房门见段绶已在等候回禀,说崔夫人遇刺一案苏州府衙已审问清楚。
“……那几名刺客起先只说是图财害命,用刑後才肯招认,背後确实有人指使,但因幕後之人并未露面,他们只知道那人来自金陵,其馀的再审不出来什麽了。属下誊录了一分供词,请殿下过目。”
晏朝接过,大致浏览一遍,颔首道:“本宫知道了。意料之内的事。”
几个劫匪而已,还不足以令真正的幕後之人暴露身份。她原已经猜到七八分,兼之此事本就不宜大张旗鼓,目前只得压下不提。
“供出来的那个主使大概也是查不到的,既然招t供是谋财,那就按劫盗判刑,不必再大费周章了。”
段绶会意,领命退下。
梁禄立在一旁,沉默半晌忍不住道:“殿下,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吗?况且他们已经盯上了崔夫人,难保不会有第二次……”
“你跟在本宫身边这麽多年,这件事倒还不至于看不明白。只是心思全放在崔氏一人身上,未免有些急躁了。”晏朝觑他一眼,梁禄讪讪垂首,低声应了个是。
“无论如何,崔氏既见过本宫的面,便至少不能在濯园出事,自然也包括归家途中。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人敢派刺客堂而皇之地劫杀,外头明里暗里不知道多少人盯着呢。加之眼下情形,这种事就不宜公开丶也没必要细究。”
“本宫与他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只看谁沉得住气罢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暂且静观其变是最稳妥的法子。”
晏朝眉梢一动,有些意外,林瞻?
。
前厅静得落针可闻。
朱庸行安坐在椅子上,时不时瞥一眼身旁的林瞻,见他依旧平和沉静,神态自若,虽是初次拜见太子,却并无半分惶惧局促之色。
地方上区区一名八品小官,心里明知被故意压制多年,如今面见储君无有愤懑,若非被官场倾轧磨平了棱角,便是看透世俗老练通达了。
两人等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忽闻几声脚步,帘子密密一响,身着常服的太子款步而入。翼善冠,盘领窄袖袍,玉带,织金蟠龙纹,庄重而尊贵。正式见官员她向来不敢轻慢,才上身的燕服便不得不脱了重换。
两人即刻起身下拜行礼,晏朝道了句平身,衆人落座,晏朝方望一眼朱庸行:“看来朱巡抚今日是为他人而来。”
朱庸行略一躬身道:“殿下英明。林瞻已复职,对于前些日子那场民乱,以及其背後的赋税之弊,他最清楚不过,是以想当面禀予殿下。”
于是目光移到林瞻身上,他起身深深一揖,先道:“巡抚大人高看,下官惭愧。”
晏朝平声道:“且先不必自谦,你既能得巡抚青眼,则必有过人之处。本宫愿洗耳恭听。”
林瞻连说不敢,复又施一礼,正色回话:“太子殿下容禀,微臣在苏州府下各县衙任县丞已近十年,期间亲见大大小小民乱不下十次,究其缘由,或是朝廷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或是灾荒之年冻饿饥馁走投无路。这一次的民乱由重赋丶洪灾及去岁雪灾引起,其中赋税乃其根因。多少农户田中颗粒无收,百姓叫苦不叠,官府只晓得遮掩镇压粉饰太平。自年初起,便不断有流民涌动,州府治安受到影响,是以民乱的规模较大,暴民围攻了府城,虽然最终被官兵镇压,但战况十分惨烈,死伤大多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暴民愤慨之下曾伤过府衙官吏,不过微臣才听闻,朝廷发旨问罪查处,伤的最重那几人罪责亦是最重。”
晏朝摆手打断:“那麽依你之见,赋税之弊又该从何处入手解决呢?”
“微臣以为,除却清丈田地丶招抚流民丶减免税粮外,漕粮运输作为江南逋赋的重要负担,亦不应轻视。臣任治农县丞提督农务丶催征税粮,忙碌时亦偶尔被调借去负责过税粮解运。苏州府县粮额浩大,目前各县治农官数量过少,加之有旧例不许治农官插手部运,税粮催征和解运环节分离,逋赋只会愈来愈重。是以,臣奏请令治农官可兼部运之责,此是其一。”
“现今漕运仍采取支运法,小民参与运粮即可免纳当年税粮,反之,纳税粮则可免除运粮。然而江南小□□粮费时费力,有的往返运粮竟需一年之久,极其不便且耽搁农时。臣奏请令江南税粮可直接运往附近卫所,後由漕军运抵京城,其间可给予耗米及道里费,如此可军民两便,此是其二。至于加耗则例,可以远近为差,臣蜗居小县眼界狭隘,需请殿下及各位大人具体商榷定夺。”
“臣愚以为,官田重赋暂时无法彻底减轻,但可以从重额官田与轻额民田的差距入手,减轻贫户税粮。即以折色银和官布折纳部分税粮。贫户可用一两银抵四石米,一匹阔白棉布平一石米。例如,重额官田与贫户中,每亩科则六七斗以上者两税可全折银布,四五斗者半数,一二斗及轻额民田仍纳本色。因银两与布匹运输便宜,亦可减轻小民负担。此是其三。”
“此外,每岁的银布至少在正月十五後开始征收,可令百姓在冬季纳过米粮後有馀粮过年。农家牲畜到二月可卖出用以纳银,纺织棉花用以纳布,到四月後再解运至朝廷,如此错开时间征粮,也好使百姓筹措宽裕。至于各地情况不同,便需因地制宜,如昆丶嘉等地田土高仰不宜种植五谷,多种木棉,常熟丶吴江等地则不産棉布,可纳金花银。”①
“以上三条乃臣愚见。而各府县中具体情况更为错综复杂,臣位卑术浅,不足洞察。”
言罢虽是谦辞,但以他的经历来看,这些经验策略已足够令人惊叹。他从容陈述时,并不是一介区区县丞,而俨然是站在整个江南山水,沿水陆通衢,立田间垅上,言辞激扬。
朱庸行双目含光,殷殷望他一眼,不由抚掌道:“此法堪称良策。林县丞一番真知灼见,真令人茅塞顿开呀!”
晏朝亦油然赞道:“果如巡抚所言,如此人才,未曾委以重用,屈居一隅,是朝廷之过。”
“殿下谬赞。既食君禄,当尽君事。上为君分忧,下为民谋利,是臣职分所在。”
林瞻立在堂中,常年操劳的背稍有些弯,一副脊骨棱角分明,首尾冠服一丝不茍,面容瞧着比年岁老,偶尔显露一双历经风霜的手。
晏朝点一点头,道:“林县丞所举之策,本宫需同诸位官员再行商议,你可先拟一篇策论详细陈言。”
“臣遵旨。”
她继而看向朱庸行:“既是巡抚举荐之人,便由你多费心了。”朱庸行应是。
晏朝擡一擡手,正欲开口命林瞻坐下,却不料他突然跪地,叩首道:“臣今日求见,还有一事,特来向殿下请罪。”
厅内气氛似是霎时凝滞,连朱庸行亦不免沉下神色。晏朝平静擡眼,唔了一声问:“你请什麽罪?”
“臣因失职在狱中待罪,内子崔氏鲁莽,竟贸然登访濯园,臣恐她言行无状,失礼于殿下,有损殿下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