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皇兄说他心悦我明华 > 晋江首发 100营养液加更(第3页)
晋江首发 100营养液加更(第3页)
如今的云棠难道不算发自本心吗?
李蹊认为,算。
即便有朝一日,云棠若找回失去的记忆,依她刚烈的个性,说不准要对他刀刃相向,但彼时的恨与此刻的爱并不冲突。
他需要做的,是让她永远遗忘下去。
待到七老八十丶鸡皮鹤发的年纪,就算云棠醒来要一刀捅死他,这一生也已过去,他没有遗憾。
那丹药是国师所出,虽一直传言没有解药,但唤水师承张沉的医术,能解一半毒性,他不信国师真的没有解药。
前朝皇妃因此丹药而死,是因为先帝要立父皇为帝,子幼母强于国祚有损,是故要杀母留子,而并非此丹药之故。
思到此处,擡头恰好看到云棠穿着一身品月色缎平银绣八团宝相纹大氅,怀里抱着一大捧凌霜而开的红梅跑了进来。
她跺了跺脚,抖落一身的风雪,唤水取下她的大氅,转身又去拿花瓶。
“殿下,昨夜刚开的红梅,我剪了几支还带着花骨朵的,放在殿内能开很久。”
云棠一边说一边往太子的方向走。
梅香浮动,清幽之处远胜其他熏香,他取过一支闻了闻,便让唤水拿去修剪丶插瓶。
温暖的双手揉着她冻红了的手,“听闻国师在大相国寺开坛讲经,想不想去凑个热闹?”
自从数月前遭遇刺杀後,云棠就不大愿意出门了,连东宫的宫门都没出过,骤然听他提说要出去,心中犹豫。
唤水站在窗边修剪梅枝,听闻国师名号,手下剪子不甚剪到皮肉,一阵刺痛血珠子冒了出来。
“放心,大相国寺有重兵把守,当日的那波逆贼也已经伏法。”
太子捂热了她的手,又递过去一盏热牛乳,那牛乳中又放着几颗他方才剥的松子和杏仁,吃起来便不单调。
“那波逆贼受谁指使?为什麽要刺杀你?”
朝堂之事,李蹊不欲多言,谁是幕後主使,他心中明了,大理寺能查到的,不过皮毛而已。
郑更将那份证供呈上去,挨了陛下几句训斥,又打了二十板子。
这事如此处理,虽不体面,却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台阶,大家彼此顺着都下来了。
“是已贬黜的崔氏罪臣豢养的家奴,崔氏富可敌国,如今半数收归国库,定然要反扑。”
云棠不知政事,听他如此说,并未起疑。
“听说大相国寺的後山有一株三百年的老榕树,枝干茂密如伞盖,许多人都往上抛红绳丶金锁,求一个百年好合。”
李蹊闻言,撩起眼皮觑她,“那你要去求吗?”
“缘何不求?”云棠放下茶盏,“去都去了,顺手的事儿。”
李蹊笑得肩膀都在抖动,清朗的笑声似从胸腔里迸发出来。
“你笑什麽?”云棠推了推他,“你再笑我不去了。”
“去去去,顺手的事儿。”
他喜欢,并沉醉于云棠以如此稀松平常的口吻,去言说彼此之间的相处。
她对两人关系这般自然的认定,让他觉得安心之馀,心中更是柔软丶熨帖。
长臂轻揽,将人纳入怀中笑着说话,不时执手亲吻。
殿中地龙已开,一室温暖如春,青铜镂空的香炉里冉冉升起缕缕白雾。
窗边的翠绿枝条舒展,花苞如胭脂点染,映着窗外纷纷扬扬的白雪,清冷中透着几分灵动,别有一番意趣。
这样的日子当真如美梦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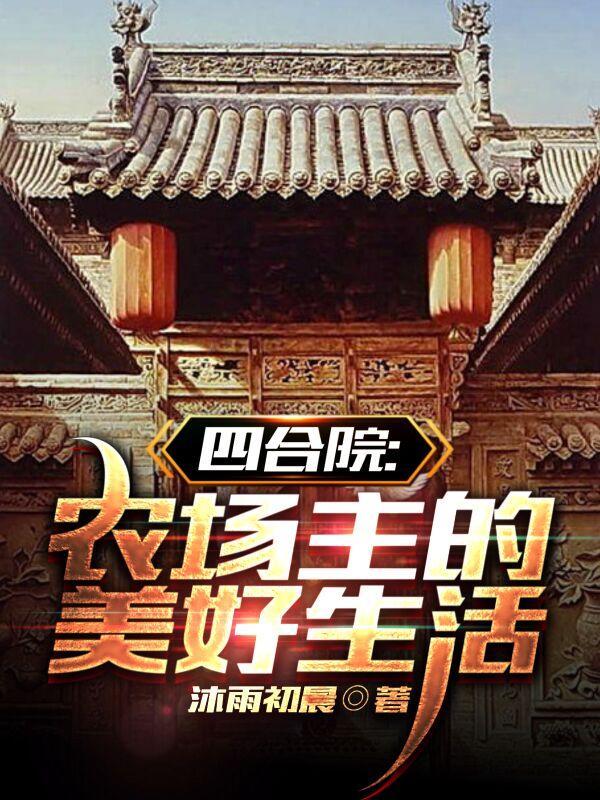
![(综漫同人)[阴晴不定大哥哥]所以和魔法师邻居恋爱了+番外](/img/5384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