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悬黎千钧什么时候出 > 缱绻情丝 萧悬黎我们前世就该这样纠(第1页)
缱绻情丝 萧悬黎我们前世就该这样纠(第1页)
缱绻情丝萧悬黎,我们前世就该这样纠……
悬黎小院里不知何时种的木芙蓉已经盛放,随风摇曳,此花味淡,微风没能卷出半点香气。
悬黎只觉自己的心也随着这一簇淡粉起起伏伏。
但木芙蓉有根,不会被风连根拔起,悬黎心里亦有数,任凭心湖荡起多少涟漪,她自岿然不动。
“对,我那时起知道了,你是姜庾楼。”悬黎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抽回手时还不着痕迹地在姜青野掌心挠了一把,“我这些日子以来的推拒忸怩纠结都是装出来的,枢密使想如何呢?”
萧悬黎眼波流转之间,散发了些有别于以往的妩媚,有些不可方物,让姜青野目光发直,根本挪不开眼。
只是这抹风情没达眼底,萧悬黎的眸子深处一片冰冷。
姜青野忍俊不禁,压不住嘴角,像把对悬黎的感情揉进了骨缝里,再借着眼神丶指尖丶眉峰的微澜,一点点漫出来,浓得化不开。
北境小将军鹰隼目光落过去的瞬间,却像被温水浸过,软得能盛下漫天星光。那双眼瞳像含着层薄雾的湖,湖底因为萧悬黎一个轻微但的举动炸开细碎的光,漾得满湖都是暖意。
姜青野指尖在半空顿了顿,最终轻轻捏住了悬黎的耳朵。那一下轻得像风扫过。
他指节泛白,明显是用了力的,悬黎却并不觉得疼,只是耳廓一片温热。以悬黎的角度,能够看见姜青野喉结滚动了一轮她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姜青野肩膀微微塌了下,像是满腔的不舍被生生抽出去一些,只馀下指尖残留的温软,在他手心里烧出一片滚烫。
姜青野摩挲了下悬黎的耳廓,悬黎不闪不避地仰头去寻他的眼睛,先看到的是他嘴角慢慢扬起个极浅的弧度,再向上看,仿佛有什麽从他眼底深处一点点晕开,染得眉梢都带了甜。
在这一刻,悬黎好像突然捉住了些属于姜青野细微的丶克制的丶却又绷不住往外溢的情绪。在他每个眼神流转丶每个指尖轻颤里,让人心头跟着一软,他好像是要告诉她藏在他努力克制之下的,是怎样汹涌的一片海。
好像酿了二十年的酒,终于在这个夏天还了她二十载的辛劳一个酣畅淋漓的甘醇。
悬黎的的一双青白玉瓜果型耳饰搭在姜青野掌心也成了温热的。
他又拈了一下才恋恋不舍地松开双手,语气里颇为遗憾却又带着无尽的期盼,“萧悬黎,我们前世就该这样纠缠才对。”
何须因朝政那等莫须有的小事剑拔弩张,他们合该耳鬓厮磨,合卺交杯。
“一身凛然正气的人是做不来这一套的,你为何一定非要让我用恶意去揣度你呢?前世那样的立场,都没能让我觉得你不可与谋,如今自然更不会了。”
“我知你在顾虑什麽,愿身化绕指柔,融大凉萧家挺得最直的一根傲骨,北境凶鹰的脚镣,从前世起,你已经铸成了,今生他不会再噬人了。”
姜青野话锋一转,“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得陪在这猎鹰身边。”
姜青野说起话来像在打哑谜,但是悬黎听懂了,硬摆出来的风流无羁溶了一层水,她说:“我记得,前世你坏过我一桩婚事,那险些被我榜下捉婿的青年才俊,是当朝状元郎,名唤拂冲。”
“老师。”杜拂冲虽形容狼狈起却身姿挺拔,只是身量不算高,脸上也一团孩气,无遮无挡的日光毫不避讳地与他亲昵,豆大的汗珠淌下来也并不去擦。
汗水几乎要浸透布袍时,钟太傅长长的甬道内现了身,杜拂冲上前行礼问安,面上没有半点不耐的情绪。
钟璩板着的脸缓和了些,他略一颔首,“事出突然,带累你遭这一番罪。”
杜拂冲仍旧躬着身,态度谦卑恭敬。
“明年三月,你便下场吧,早早入仕,替陛下分忧。”钟璩拈须,一副深谋远虑的模样。
“学生年岁尚轻,恐难入围。”杜拂冲一板一眼,钟璩看得出来,这不是谦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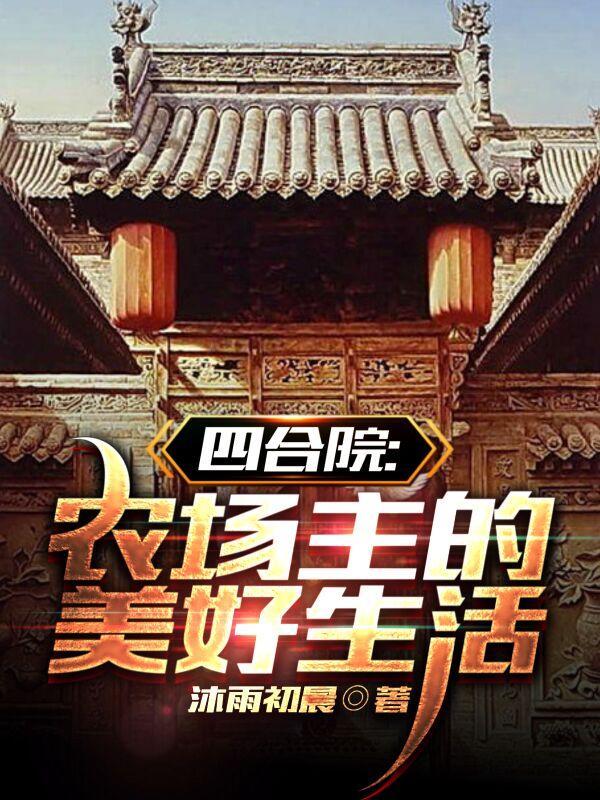
![(综漫同人)[阴晴不定大哥哥]所以和魔法师邻居恋爱了+番外](/img/5384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