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以你为欢 > 第 2 章(第2页)
第 2 章(第2页)
等了半分钟,一个戴了副银边眼镜,大约五十岁上下,皮肤有些白的过分的女人开了门。
她正拿着手机轻声说话,眼梢粗略地扫了两人几眼,神情没发生任何变化,直到挂了手里的电话之後,才将目光结实地落在沈颜的脸上和脑袋上。
“这是沈颜?”
沈萧掏出打火机噌地一滑,点了根烟,“不然呢?这就是你女儿跟别人的种,你想改名改姓都行,随你,之前说好的,按照岁数把养育费给我,人钱两清。”他空着的那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摩挲了下。
丁进不屑和沈萧多费口舌,比了个稍等的手势,“你等我会。”再回来时,她手里多了沓厚信封和一张纸。
“这是合同,你放心,上面内容只是表示孩子跟了我,你日後没有正当理由的话不能要回去,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录音拍照。”
沈萧一把抽过那那沓钱点了下塞进口袋:“真不愧是律师~用不着这些花里胡哨的,我要个不是自己的种做什麽?”
他歪嘴笑了下,曾经棱角分明的轮廓被自私愤恨遮的面目全非。麻利地在纸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他拍了拍沈颜的肩膀,用了点力气,“沈颜,这以後就是的家了,有事没事找你外婆。”末尾语调轻快,听得出他的心情在迅速的飞扬。
背上的温度很快散去,沈颜的馀光看着沈萧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她就这麽被当着面“交易”掉了。
“进来吧。”
丁进没说什麽客套话,语气也不轻柔,没有温度的镜片後的目光很犀利,仿佛能直接穿透人心,沈颜莫名在她身上看到了几分丁果的影子,麻木的神经有了片刻的松动,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丁进家里有位客人。
那是个穿着短袖白衬衫和牛仔裤,差不多高中生模样的少年,眉眼俊气温润,仔细看还是粗糙看,看几眼都是个帅哥。
他双手捧着一杯白开水,眼神盯着面前的茶几,从开始到沈颜进来,动作变都没变,等注意到沈颜的目光,才擡起上眼睑,朝她露了个礼貌性的浅笑。
这个笑非常好看,比沈颜见过的任何一个男性都要好看,甚至可以称之为漂亮,可沈颜却清楚地看见,他的笑意没有达到眼底,温和的表象下,大约是极致的冷酷。
丁进朝沈颜介绍,“这位是薄金修,长你几岁,你得叫声哥哥。”
薄金修脸上笑意未停,沈颜此刻却没心情,毕竟当着陌生人的面被“卖掉”,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何况对方的态度并没有多热络。
她沉默多时,还是没开口,丁进也没勉强,领着沈颜进她的新房间,脚下的拖鞋很软,踩在地板上空落落的,很不踏实。地板是木质的,周遭的装饰丶摆设,家具亦是如此,老式干净,处处透着沉闷的气息。
她的新房间不大,摆设简单,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靠床头那面墙上有贴过东西的痕迹,窗户对着楼下过道,窗帘和床单都是浅绿色的,床头柜上摆了台复古风的台灯。
“你先把带来的行李归置归置,缺什麽可以先列个清单。”
丁进开口没有过多的修饰,她表情平淡,“我就在客厅聊事,有需求随时找我”,随後推门出去。
沈颜来不及回应,她的背影已经无声地走远。她站立原地半晌,嗅着屋内陌生的淡淡的味道,伸手摸了下桌面,很干净,但也透着股很久无人问津的气息。
天气依旧阴沉,屋里闷得热像个蒸炉,一点风影都没有。
沈颜爬上飘窗,将窗户开到了最大,脸上拂来那麽几丝夹着水汽的风,不仅没降热,反而勾起了烦躁的情绪。
客厅传来丁进和那个客人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两人声音都很小,不足白镇人均分贝的千分之一,沈颜打开行李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初来乍到,身体的本能让她下意识地接收着周遭的一切信息,耳边忽然传来“遗産”丶“原告”之类的字眼,沈颜一下子想起来,沈萧不久前才说过,丁进是个律师。
律师这个职业,从前在沈颜心里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现在也是。
行李拿到一半,她走了神,里面的衣服和耳机线混结成一团,她一抽全给扯了出来,“哗”的一声,没闭合的笔袋撒了一地,稀里哗啦的声音持续了好几秒,但在沈颜脑里,那几秒堪比几小时,沈颜感觉空气都凝固了一瞬。
她提着气,没收拾,等了几分钟才喘了口气,蹲下身子去捡东西。几支笔滚的七零八落,一只圆头水性笔停在了门边,沈颜探过身子去够,脑袋触到没关的门缝,一句话忽然飘过来,“谢谢丁老师,我妈的葬礼在下周三,要是你有时间的话,我想她会很愿意你送她最後一程的。”
“我会去的。”
两个人的语气都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很快传来门开啓又被关上的声音,而几乎在同时,屋外由远及近地忽地亮起道闪电来,雷声轰地一声在耳边炸开,顷刻豆大的雨珠砸了下来,沈颜失神地转向窗外,脸上被刮了几滴雨水。
沈颜这才反应过来去关窗,窗户扣有些年头,沈颜靠近了使足了力气才堪堪关上,吁气低眉间,眼底下掠过那个少年撑着把黑伞的身影,雨愈来愈大,视线被模糊地几乎看不清,少年踩进浅水坑里,很快就看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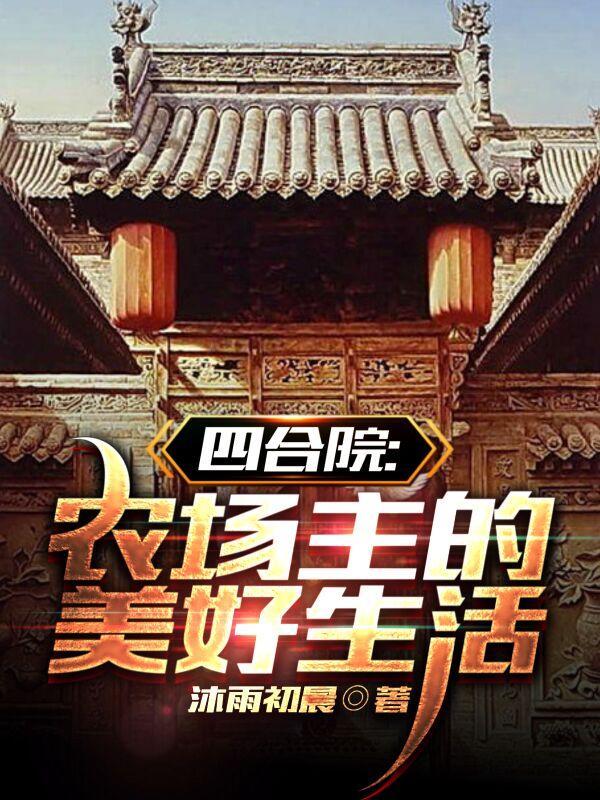
![(综漫同人)[阴晴不定大哥哥]所以和魔法师邻居恋爱了+番外](/img/5384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