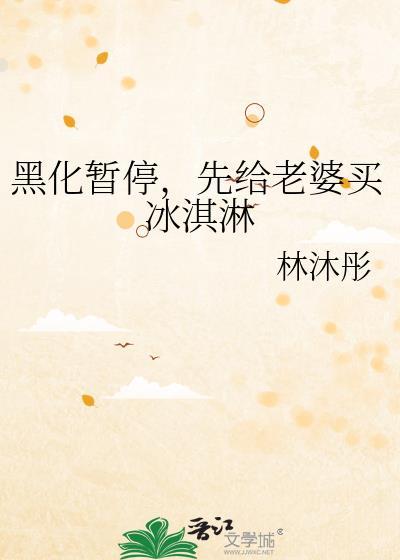紫夜小说>盛世至尊酒 > 第57章 永王之乱(第1页)
第57章 永王之乱(第1页)
永王那封措辞含蓄却杀机凛然的威胁信,如同一块被投入平静湖面的千斤巨石,在伍元照的心湖深处激荡起千层骇浪。信纸是上好的薛涛笺,带着淡淡的冷梅香,字迹是永王一贯的雍容端方,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寒意,却让伍元照指尖冷。她面上不动声色,甚至唇角还维持着一抹惯常的、恰到好处的温婉弧度,只有贴身侍奉多年的崔嬷嬷,才能从她骤然收缩又缓缓舒展的瞳孔中,窥见那一闪而逝的惊涛。
她纤长的手指缓缓将信笺折好,收入一个不起眼的紫檀木小匣中,动作优雅如常,仿佛只是收起一份寻常的家书。然而,当匣盖合上的轻微“咔哒”声响起时,她心中已有了决断。
“嬷嬷,”她声音压得极低,如同耳语,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凝重,“传我的话,自今夜起,承香殿内外守卫增加一倍,特别是后殿窗牖及通往皇子们寝殿的廊道,必须十二时辰有可靠之人值守。夜间巡逻,改为两炷香一轮,巡逻路线交错进行,不许有丝毫规律可循。所有轮值护卫,饮食需经专人查验,不得食用外间送入之物。”
崔嬷嬷心头一紧,她伺候皇后多年,深知这位主子心性之坚韧,若非事态严重至极,绝不会如此兴师动众,连饮食这等细微处都顾虑周全。她不敢多问,只肃容躬身,低声道:“老奴明白,这就去安排,必不让任何宵小有可乘之机。”
是夜,承香殿依旧灯火通明,宫人们步履轻盈,一切如常。但只有伍元照自己知道,这一夜,她睡得极浅。锦帐内熏着安神的百合香,却抚不平她紧绷的神经。窗外风吹过竹叶的沙沙声,远处更鼓敲响的梆梆声,甚至殿宇梁间偶尔传来的夜鼠窸窣,都能让她瞬间惊醒,手不自觉地向枕下摸去——那里,藏着一把锋利的匕,是皇帝昔年所赠。她侧耳倾听,直到确认那只是寻常声响,才缓缓松开握住刀柄的手,掌心已是一片冰凉的湿濡。黑暗中,她睁着眼,望着帐顶模糊的绣凤纹样,脑海中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生的险情以及应对之策。永王的势力盘根错节,既然敢递来威胁信,必然是有了相当的把握,她绝不能坐以待毙。
【系统提示:侦测到敌对势力“永王集团”的明确威胁。触防御任务“暗箭难防”:在小时内加强安全防护,避免遭受暗杀。任务奖励:积分ooo点,被动技能“危机感知”等级提升。】
系统的提示音冰冷而清晰,更印证了她的判断。这不是宫闱内惯常的勾心斗角,而是你死我活的杀局。
次日清晨,天际刚泛起鱼肚白,伍元照便如常起身梳洗。铜镜中映出的容颜,依旧明艳端庄,眼底那一丝难以察觉的青黑,被巧手的宫女用细腻的珍珠粉精心遮掩。她选了件湖蓝色绣缠枝莲的宫装,色泽清雅,能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的沉稳气度,又不会在即将到来的端阳盛宴上抢了皇帝的风头。
她先去偏殿看望礼弘和礼贤。两个小家伙正由乳母喂着吃牛乳蒸蛋,见到母亲进来,立刻丢下银匙,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咧开没长齐几颗牙的小嘴,甜甜地叫着“娘亲”。礼弘已经能摇摇晃晃地走几步,扑过来抱住她的腿,仰着红扑扑的小脸傻笑;礼贤则坐在特制的高脚椅上,咿咿呀呀地流着口水。伍元照心中一软,蹲下身将两个孩子都揽入怀中,感受着他们温软的小身子和纯粹的依赖,一股强烈的保护欲油然而生。她亲了亲他们柔嫩的脸颊,心中暗自誓,无论付出何种代价,绝不让永王或其他任何人的黑手,伤害到她的孩子分毫。这深宫再冷,再暗,她也要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然的天地。
用过早膳,伍元照按计划在承香殿的东偏殿召见太子礼忠。太子准时到来,身着符合制度的淡黄色四爪蟒袍常服,举止礼仪无可挑剔,躬身行礼时,连衣袍褶皱的幅度都恰到好处。
“儿臣参见母后。”少年的声音清朗,却带着一丝刻意保持的疏离,如同在两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界限。
伍元照心中微叹,她如何不知这孩子的症结所在。皇帝对幼子的偏爱几乎不加掩饰,加之有心人有意无意的挑拨,使得这位日渐成长的太子,对身为嫡母又育有幼弟的她,心存芥蒂,日益敏感。她面上不露分毫,温和地抬手虚扶:“太子不必多礼,坐吧。”
内侍搬来绣墩,礼忠谢恩后,仅坐了半边,腰背挺得笔直。
伍元照端起茶盏,轻轻撇去浮沫,状似闲话家常:“太子近来在东都住得可还习惯?崇文馆的课程紧,若觉得吃力,可向太傅直言,切勿积劳。”她的语气充满关切,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寻常问候。
礼忠垂眸,恭敬回道:“谢母后关心,儿臣一切安好。太傅教导精心,儿臣虽资质愚钝,亦觉受益匪浅,不敢言劳。”
问答间,透着官样的客套。伍元照放下茶盏,目光似是不经意地扫过殿外庭院中的一株石榴树,花开正艳,如火如荼。她语气依旧温和,仿佛只是随口一提:“本宫听闻,永王府在东都的别院,与太子你的府邸相距不远。永王是长辈,太子平日里可曾有过往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礼忠微微一怔,显然没料到皇后会突然问起永王。他迅抬眼看了伍元照一下,又立即垂下,谨慎地斟酌着词句:“回母后,永王叔公近年来深居简出,潜心礼佛。儿臣只在年节宫宴及宗室定省时,按制前往拜见,平日并无私下往来。”他回答得滴水不漏,既表明了恪守礼制,又撇清了与永王的亲近关系。
伍元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指尖轻轻敲击着光滑的紫檀木桌面,出几不可闻的嗒嗒声。她沉默片刻,方轻声道:“永王毕竟是长辈,又是宗室元老,太子若得闲,多走动问候亦是孝道。只是……”她刻意顿了顿,目光若有实质地落在太子身上,观察着他最细微的反应,“如今朝中多事之秋,漕运案余波未平,太子身为国本,与人往来,尤其是宗室中的长辈,还需多加谨慎,明辨是非才好。”
礼忠眼中掠过一丝不解和困惑。皇后这话,前言让他亲近永王,后语又让他提防,究竟是何用意?他毕竟年轻,虽敏感于自身地位,但对朝堂深层博弈的凶险,认知尚且不足。但他素来谨慎,虽不解深意,仍恭顺应道:“儿臣谨记母后教诲。”
伍元照知他未必真能领会自己的警示,但有些话点到即止,过犹不及。种子已经播下,只需静待时机芽。她不再多言,转而询问太子近日读《资治通鉴》的心得,又赏了他一方御赐的上好紫玉端砚,勉励几句,便让他退下了。
太子离去后,偏殿内恢复寂静,只余熏香袅袅。伍元照独自坐在窗前,望着太子远去的身影,陷入沉思。从太子的反应来看,他确实对永王的勃勃野心和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在他心思纯良,并未卷入永王的阴谋,不至于让她面临父子对立的人伦惨剧;坏在他毫无防备,如同一张白纸,极易被永王这等老谋深算之辈以亲情或利益蛊惑利用,届时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尽快让太子,至少是让皇帝,对永王有所警觉。
午时刚过,日头正烈,杨夫人便匆匆递牌子入宫。她虽是皇后生母,有出入宫闱的便利,但如此急切,必是有要事。伍元照屏退左右,只留崔嬷嬷在门口守着。
杨夫人连茶水都顾不上喝,便压低声音,面色凝重地道:“娘娘,有紧要消息。我们安插在永王东都别院的眼线,今晨冒死传来急报,昨夜子时前后,有一批约莫十数人的黑衣人,趁着夜色秘密潜入别院后角门,直至今晨天蒙蒙亮才分批悄然离去。行事极为诡秘,若非我们的人一直紧盯,几乎难以察觉。”
伍元照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可探听到些什么?”
杨夫人凑近几分,声音更低:“眼线冒险靠近书房窗外,只听得只言片语,似乎提到了‘清除障碍’、‘时机将至’、‘一击必中’等语。因怕暴露,未敢久留。”
“清除障碍……”伍元照轻声重复着这四个字,指尖凉。永王果然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动作如此之急!她冷静追问:“可知那些黑衣人离去后的去向?”
杨夫人摇头,脸上忧色更重:“他们极为警觉,出了别院便分散潜入各条巷陌,我们的人不敢跟得太紧,怕打草惊蛇,反害了眼线性命。不过,领头的一人,在进门卸下兜帽的瞬间,被眼线瞥见侧脸,记下一个明显特征——左脸颊上,有一道寸许长的狰狞刀疤,从颧骨直划到下颌,很是骇人。”
“刀疤脸……”伍元照默默记下这个关键特征,立即唤来崔嬷嬷,低声吩咐:“去,让护卫领挑选绝对可靠、身手敏捷且面孔生疏的心腹,换上便服,暗中查访东都城内,特别是城南三教九流混杂之地,近日是否有一伙脸上带刀疤的江湖人士活跃,查清他们的落脚点、人数、以及近日动向。记住,只可暗中监视,万不可轻举妄动。”
“是,娘娘。”崔嬷嬷领命,快步离去。
杨夫人又道:“还有一事蹊跷。眼线还报,永王别院这几日以府中仆役染疫需防治为由,通过不同药铺,采购了大量药材,其中不乏三七、血竭、白药等治疗外伤的极品金疮药,数量远寻常所需。老身怀疑,他们恐怕不只是在做准备,更可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行动,预备事成之后或失手之后的救治之物。”
伍元照眸光一冷,永王这是要破釜沉舟了。她沉吟片刻,脑中飞盘算,随即开口道:“母亲,情势紧迫,我们不能只被动防御,需得双管齐下。一面加强自身防范,另一面,要主动出击,搅乱他们的布局,逼他们露出马脚。”
“娘娘的意思是?”杨夫人凝神静听。
“永王欲‘清除障碍’,其目标不外乎三者:陛下、太子,或本宫与两位小皇子。”伍元照冷静分析,如同在棋盘上推演,“陛下身边禁军林立,暗卫如云,守卫森严,他们难以得手;太子虽防备稍弱,但刺杀当朝储君目标太大,极易引火烧身,震动天下,若非万不得已,永王不会行此险招;那么,最可能、也最容易制造混乱的目标,便是本宫和礼弘、礼贤。若能得手,既可重创陛下,又可造成宫廷大乱,便于他浑水摸鱼。”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杨夫人面色骤变,急道:“这该如何是好?娘娘和两位小皇子万金之躯,岂可置身险地!”
伍元照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眼中锐光乍现:“他们若以为本宫是那等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便是大错特错了。本宫执掌凤印,统领六宫,岂是易与之辈?”她顿了顿,吩咐道:“母亲,你即刻让手下信得过的言官和市井耳目,巧妙地散播消息,就说漕运案的追查又有新的重大现,似乎牵扯出地位更高的幕后主使,意图动摇国本。但切记,消息要放得模糊,语焉不详,只让人隐约感觉风波未平,且暗流指向更高处,却猜不透究竟具体指向哪位宗亲重臣。”
杨夫人略一思索,明白了女儿的意图:“娘娘这是要打草惊蛇,引蛇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