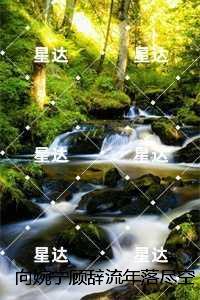紫夜小说>南屏旧桥是什么意思 > 第64章 叩天鼓一声冤难诉惊堂木三响义不存(第1页)
第64章 叩天鼓一声冤难诉惊堂木三响义不存(第1页)
天是从一线死灰,慢慢被染成青白的。
我坐在窗边一夜未眠。晨间的冷风带着水汽,穿过破旧的窗棂吹在我脸上,却吹不散我心头那股由滔天怒火冷却后凝结成的寒冰。
我不再是那头蛰伏的兽了。
兽靠的是本能与爪牙。而我此刻需要的是猎人的头脑。
一个能精心编织罗网,冷静等待时机,一击便要将猎物的心脏彻底洞穿的头脑。
我在客栈这方寸之地来回踱步。脚下的木板出“吱呀”的轻响。
摆在我面前的,是三座大山。
第一座山,名为“证据”。
宝珠的伤是证据。可她被囚于赵府深院,我总不能将一个“疯癫”的妇人强行拖上公堂,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袒露一身的伤痕。那对她,是二次的凌辱。赵家只需一句“夫妻口角,失手所致”便能轻易揭过。
林家的家产是证据。可契书文书,皆在赵家之手。他们既然敢做,就必然做得天衣无缝。我空口白牙,谁会信我?
赵铭害死腹中胎儿,更是铁证。可唯一的证人,只有宝珠。一个被他们牢牢掌控在手心,随时可以被扣上“失心疯”帽子的可怜人。
第二座山,名为“权势”。
赵家,在京城经营多年,早已盘根错节。赵铭的父亲,是户部侍郎赵德言。掌管天下钱粮的衙门,与掌管律法刑狱的刑部,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却也互通声气。我昨夜探听到的消息中,刑部侍郎吴仁义,便是赵家的座上宾。
官官相护,自古皆然。我一个无名小道姑,想在这张早已织好的大网中撕开一道口子,难于登天。
第三座山,也是最险峻的一座,名为“时间”。
宝珠还在喝那能让人痴傻的药。她的身体,她的神智,都在被一点点地蚕食。我等得起,她等不起。我必须与阎王赛跑。
将这三座大山在心中反复掂量后,我的脚步停了下来。
窗外的天光,已经大亮。集市的喧嚣,隐隐传来。
这人间烟火,最是迷人眼,也最是藏污纳垢。
我心中,已有定计。
既然前路被大山阻隔,那我便另辟蹊径。一路向阳,一路往阴。
明面上,我要走一条最正也最难的路。我要去击鼓鸣冤。
我并非不知此路凶险,更知此行十有八九是徒劳无功。赵德言是户部侍郎,我告不倒他。但我可以告他的儿子赵铭。民告官,难。但民告民,官府总得受理。
我不要赢。
我要的,是“告”这个举动本身。
我要将赵家的这桩腌臢事,从他们密不透风的后宅里硬生生地拽出来,摊在京城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我要让“清心观小道姑为友鸣冤,状告赵家恶婿”这件事,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成为茶楼酒肆里的故事。
舆论,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要做的,就是掀起这第一道微不足道的涟漪。
至于暗处……
我走到桌边,倒了杯冷茶,一饮而尽。
暗处,才是我的主战场。
我需要一个能证明当年林家产业交接有诈的人。当年的账房先生,或是林家的旧仆。京城这么大,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我需要一份能让赵家哑口无言的铁证。或是那份被动了手脚的契书副本,或是赵家这些年做的其它亏心事。
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去查探,需要动用苏世安留下的所有力量。
而连接这两条线的关键,便是张嫂。我要通过她,稳住宝珠,让她在赵府那个魔窟里成为我最重要的一枚搭档。
思及此,我心中那团乱麻,终于被理出了一点头绪。
我不再犹豫,褪下便于夜行的劲装,换上了那身洗得有些白的青色道袍。
这身道袍,上面还带着南屏山顶阳光与皂角混合的清香。
它曾是我的束缚,是我一心想要逃离的象征。
但今日,它是我唯一的铠甲。
……
刑部的衙门,坐落在京城最威严的朱雀大街上。
![灵异片演员app[无限]](/img/1882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