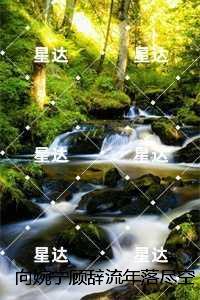紫夜小说>南屏旧桥是什么意思 > 第94章 舌尖藏冷箭深雪埋旧梦(第5页)
第94章 舌尖藏冷箭深雪埋旧梦(第5页)
刺眼的红。
那是大婚的喜堂。
苏世安站在那里,一身红衫,那眼神变得好陌生。
陌生得像是在看一个路人,一个麻烦。
他对身边那个看不清面容的女子笑着说:
“哦,她啊。”
“她只是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道姑朋友。
这个词像是一把把尖刀,把我的心扎得千疮百孔。
我拼命地想喊,想问他为什么要骗我,想问他曾经那些誓言算什么。
可我不出声音。
我只能站在那场漫天的大雪里,看着他转身离去,看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
好冷。
真的好冷。
“咚咚。”
两声极轻的叩门声,像是一道闪电,猛地劈开了我的梦魇。
我猛地睁开眼。
眼前是一片漆黑的屋顶,窗外依旧是那个寒风凛冽的北疆深夜。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额头上全是冷汗,里衣已经被湿透了,粘腻地贴在背上。
心跳得快要炸开。
原来是梦。
可是那梦里的痛,却真实得让我浑身都在抖。
“咚咚。”
又是两声。
很轻,却很笃定。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强撑着下了床。
腿有些软,但我还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门口。
“谁?”
我哑着嗓子问了一句。
没有人回答。
门外只有风吹过走廊的声音。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拔下了门栓,拉开了房门。
门外空空荡荡。
那个即使是深夜也未必安宁的走廊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只有那一盏挂在楼梯口的油灯,摇摇晃晃地洒下一点昏黄的光。
我低头。
就在我的脚边。
放着一个粗糙的托盘。
托盘上,放着一个还在冒着热气的粗陶碗。
那碗里是一碗黑乎乎的汤药,闻着就苦,带着一股浓烈的中药味。
而在碗的旁边。
叠放着一件深灰色的男式棉袍。
那袍子很厚实,针脚细密,领口还滚着一圈黑色的毛边。
那是孙墨尘的衣服。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灵异片演员app[无限]](/img/1882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