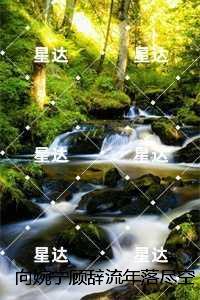紫夜小说>南屏旧桥边是什么意思 > 第75章 骤雨别南山一佩待君还(第3页)
第75章 骤雨别南山一佩待君还(第3页)
玉佩上,他残留的体温,已经被这无情的雨水,彻底冲刷干净了。
只剩下,一片冰凉。
像我此刻的心。
---
苏世安走了。
我的魂,似乎也跟着他一起走了。
接下来的几日,我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
每日依旧晨起,练功,诵经,跟着师父辨识草药,陪着静心说话。
可我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人是麻木的。
练剑时,我会对着一棵竹子,怔怔地出神,直到清云师姐在旁边小声提醒,才惊觉自己已在雨中站了半个时辰。
诵经时,满目的经文,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团团毫无意义的墨迹。我嘴里念着《清静经》,脑海里回荡的,却全是他那一句“归期未定”。
静心拉着我的手,忧心忡忡地问我:“初真,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这般难看。”
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告诉她,只是前几日淋了雨,有些着凉,不碍事。
我知道,我骗不过她,更骗不过师父。
师父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看着我,用她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沉静地看着我。
然后,她吩咐清云,去藏经阁,将那部最是冗长枯燥的《道藏辑要》搬了出来。
“初真,”师父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无波,“从今日起,你每日的功课,便是抄写这部经文。何时抄完,何时再去做别的。”
我看着那堆得比我还高的经书,头皮一阵麻。
若是从前,我怕是早就上蹿下跳地跟师父讨价还价了。
可如今,我只是默默地接了过来,道了一声:“是,师父。”
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用她的方式帮我。
她要用这最磨人性子的方式,让我静下来,让我把那些无处安放的思念与恐慌,都倾注于笔端,一笔一划地消磨掉。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便只剩下了三件事。
练剑,抄经,等待。
我常常会跑到那日送别他的山坡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就那么看着山下那条空无一人的小路,从清晨看到日暮,从云起到云落。
我盼着,能在下一个转角,看见那辆熟悉的青布马车。
可我知道,这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
那枚玉佩,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我用一根结实的红绳将它穿起来,贴身挂在颈间。
夜深人静时,我会将它取出来,放在掌心。
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那繁复的云纹,感受着那颗殷红的相思豆,那冰凉的触感,总能让我纷乱的心,稍稍安定几分。
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失魂落魄地望着山路呆时,山中那个新来的,沉默寡言的猎户,总会不远不近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一边打磨着手中的柴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在我深夜无法入眠,独自在院中练剑时,那个自称是山下村妇,每日都会虔诚地上山给三清祖师上香的大婶,会在经过清心观后门时,脚步稍稍停顿,侧耳倾听片刻,确认院内安全后,才继续前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些人,就像是融入了南屏山景色的影子,沉默地,忠诚地,执行着他们主人离开前最后的命令。
他们会定期,用我看不懂的方式,将写着“一切安好”的讯息,送往那个风暴的中心。
而这一切,我都一无所知。
---
日子,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等待与煎熬中,缓缓流过。
![灵异片演员app[无限]](/img/1882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