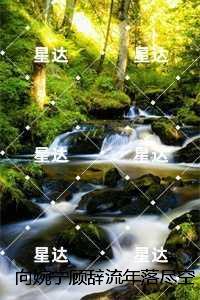紫夜小说>爱过但我选权力枕上灯 > 5060(第4页)
5060(第4页)
彩绢你想要什么颜色?阿娘去买线给你织。”
若木被九妘人奉为神树,其叶灿黄,遇光流金,无花无果,终年不败,扎根在仙鹤潭边、极高大宏伟,有直通天穹的巍峨壮阔,令人望而生畏。
“红色!”刚说出口鸠鸠就又改了主意:
“青色青色!若木上挂的红绢太多了,用红色不够显眼!
我的彩绢,到时候一定要挂到最高、最风光的位置,让大家抬头就看到!”
“好,就青色,一定让你够显眼,出尽风头。”阿云若掐了掐女儿的肉脸,面上露出一点笑意。
“阿娘,彩绢上是要绣名字的,我的名字你想好了吗?”鸠鸠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
阿云若点头:“就叫阿云隹吧,晚上我把字写出来给你,你看看满不满意。”
“我还以为会叫阿云鸠呢!”鸠鸠咧嘴一笑。
阿云若斜了女儿一眼:“你自己听听这名字好听吗。”
“不好听。”鸠鸠挠头道:“但是我从小也被叫惯了,何况做鸟儿多好,可以飞呢。”
阿云若耐心解释:“隹就是短尾巴的鸟儿,而且小而无斑之鸠,也叫隹。”
“还是阿娘懂得多。”鸠鸠满意地笑了。
阿云若拧她的耳朵:“成人礼之后我就开始教你大央的一些书文典籍,还有更多官话,你必须上心,不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作为战士,你日后是要跟商队一起出去,负责为通商之人保驾护航的,不会说话识字可不行。”
鸠鸠捂着耳朵连声应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好好学!”
可惜阿云若的彩绢还没织好,一日夜里,鸠鸠就生了场高烧,浑身滚烫,意识昏沉,找遍医者,却都无能为力。
就在阿云若绝望之际,有阿云部的商人给她递来消息,说是神医雪姑近来在沧州边陲行医,她可以领着女儿前去看诊。
阿云若连夜启程,耗费许久才找到雪姑。
雪姑人悖其名,是个肤色颇深的女子,身形健硕,面色红润,眼眸清亮,温厚善谈,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是菩萨相。
而她也的确有菩萨之能,鸠鸠身上九妘医者束手无策的高热,她只用一副汤剂便迅速退了下去。
阿云若千恩万谢,恨不得以命相报。
可雪姑不要她的命,雪姑只是摩挲着她女儿左手掌心那枚形如翎羽的赤红色胎记,好言好语,道出她女儿身世,夺走了她的女儿。
鸠鸠再醒来的时候,身边已无阿娘,只有坐在床边,用慈爱目光看着她的雪姑。
她目光在室内逡巡一圈,发现自己不在九妘,倒像是在大央领地。
“你、你是、谁?”鸠鸠的官话还说得很不标准,但她能看出身旁这个陌生人对自己并无恶意。
雪姑笑道:“我叫雪姑,是救了你的人。”
沧州话鸠鸠还是听得懂的,也比官话熟悉太多:“多谢姑姑救我,是我阿娘将我托付给你的吗?”
雪姑犹豫片刻,对她将关于身世的一切和盘托出。
鸠鸠怔愣半晌,骤然翻身下床,连鞋也顾不上穿,不顾一切冲向房外。
雪姑眼疾手快,一把揪住她:“你这是做什么?”
“骗子!拐子!放开我!”鸠鸠奋力挣扎,奈何雪姑是军伍出身,又孤身行医多年,还是成人,武艺比她强,力气也比她大,她死活都挣脱不开。
实在是筋疲力竭了,她噗通往地上一坐,张开嘴嚎啕大哭:“我要我阿娘!我要我阿娘……”
她嗓子都哭哑了,闹腾得厉害,雪姑实在没办法,只好让她领路,陪她去九妘找阿云若。
二人行到一座矮山前时,鸠鸠让雪姑停步,说九妘通路,不可为外人所知。
雪姑听过这个规矩,便也不再前进,停在原处等她。
鸠鸠七拐八拐,走过极长、分岔极多、极曲折偏僻的一段路,还走错几次,中途手掌也摔破了,耗费近一天一夜,终于见到仙鹤潭。
她伴着月光径直回家,翻过围篱,敲响家门。
窗扉处亮起烛光,房内阿云若问是谁,她一言不发,如此重复几次,屋门终于开启。
打开屋门看到女儿狼狈的脸,阿云若眼眶登时就红了,双唇颤抖着,一个囫囵字也说不出来。
鸠鸠那双圆眼睛里也盛满泪水,她吸了吸鼻子,哑着嗓子问:
“阿娘,你把我扔了,你不要我了,是不是?”
都这个时候了,她其实早就明白雪姑没骗她,只是她自己还想骗自己,非要把答案问得清楚。
阿云若偏过头去,喉间哽住,不敢看她:“你本就不是我的女儿,我得把你还给你真正的母亲。”
鸠鸠执拗道:“我只有你一个母亲,也只做你的女儿。”
阿云若紧闭双目,眼尾有泪水滑落,却狠下心肠,残忍开口:“放过我吧,也放过你自己。”
“所以,”鸠鸠的声音陡然低了下去,音调发颤:“你就是不要我了。”
她竭力想维持平静,像个大人,泪水却汹涌而下。
阿云若见她如此,心痛如绞,但仍努力维持着寻常的语气:
![灵异片演员app[无限]](/img/1882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