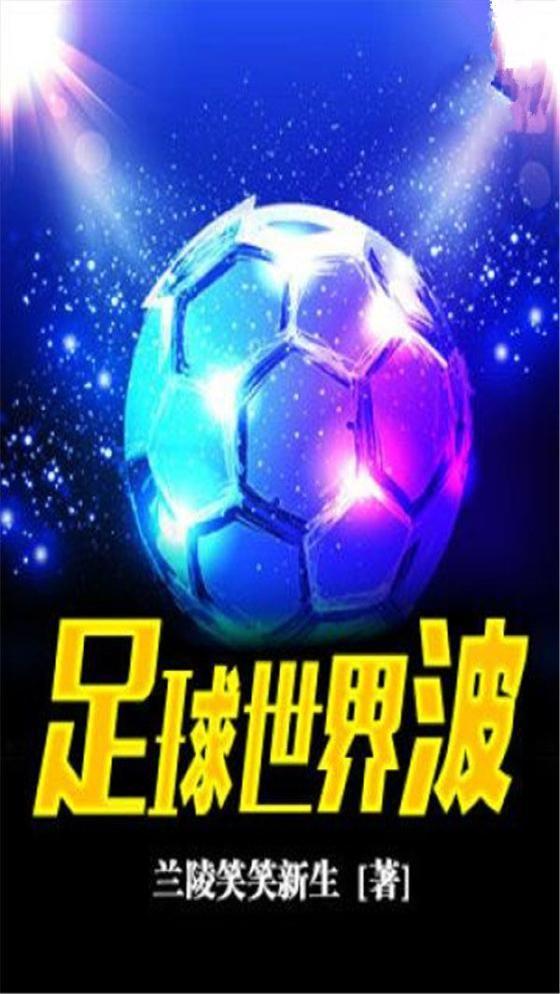紫夜小说>我的仙君是邪祟是主攻还是主受 > 第397章(第1页)
第397章(第1页)
“不……不要……”
邪神的哀嚎从幽冥之眼里炸出来。不是某张人脸的声音,是上万张嘴迭在一起的、属于本体的崩溃。巨树的根系从地底抽出,像垂死的蛇群,缠着半座祭坛往下坠。幽冥之眼的黑雾开始消散,露出里面蠕动的邪神本源——一团黏腻的黑泥,正拼命往地下钻。
箭矢击中了。
不是穿透,是“吞噬”。狐火红的箭身裹着白仙血脉的白光,撞在幽冥之眼的核心。黑泥发出滋滋的响,像被烧红的铁签扎进肉里,开始蒸发。金蓝小龙绕着箭矢转了一圈,龙吟震得天池的水沸腾,黑泥瞬间化成青烟,飘散在风里。
叶清弦喷出一口血。她的左腿再也撑不住,倒在沉砚白怀里。小白蛇图腾回到她臂弯,金蓝鳞片慢慢褪成温凉的白,像江临从前趴在她膝头打盹的样子。
幽冥之眼彻底碎裂。
变成无数黑点,被风一吹,散得干干净净。天池穹顶的裂缝缓缓愈合,雷劫的余威终于散尽。阳光穿透云层,照在翻涌的池水上,泛着细碎的金斑。血雾散了,空气里飘着桂花香——是叶红玉的桂花酿,是胡三太爷的狐裘,是所有活下来的人的希望。
“我们……赢了?”叶红玉轻声问,手里还攥着陶壶。
沉砚白抱着叶清弦,望着天池的水。他的道袍染血,却笑得像个孩子:“赢了。”
小白蛇图腾突然发出清鸣。
江临的龙吟从图腾里钻出来,带着笑:“清弦,你做到了。”
叶清弦睁开眼。
她看见天池的蓝天,看见桃花开了——是山下酒肆的桃花,是小时候红玉偷藏在袖筒里的,是江临总说要带她去看的。她摸着沉砚白的脸,指尖沾着自己的血,却暖得像他的温度:“是啊,赢了。”
叶红玉扑过来,抱住她的腰。她的脸上还沾着血,却笑得像朵绽放的桃花:“姐姐,我们回家!”
这两个字,像把钥匙,打开了所有封存的记忆。叶清弦望着身边的两个人,望着远处飘着桃花的天池,突然觉得——
所有的痛,所有的伤,所有的失去,都值得了。
新的开始
天池的风裹着桃花香,吹得人鼻尖发痒。
残垣上的冰碴早化了,滴下的水浸湿了青石板,长出细碎的青苔。叶清弦倚在江临化成的白蛇玉佩旁,右眼蒙着层靛蓝纱布——那是胡三太爷临终前扯下的狐裘,布角还沾着老人当年的龙涎香。左眼却亮得惊人,像揉进了整座桃林的星子,能清晰“看”到空气中浮动的桃花瓣,能听见沉砚白道袍上龙涎香的纹路,能触到玉佩里江临的温度,温凉的,像他从前趴在她膝头打盹时的龙尾。
江临的声音从玉佩里钻出来,带着点刚睡醒的哑。叶清弦伸手摸了摸胸口的蛇形玉佩,指腹蹭过刻着“临”字的纹路——那是她小时候用桃枝在江临狐裘上画的,没想到现在刻进了玉里。
“我在。”她轻声说,“你……还疼吗?”
玉佩微微发烫,江临的笑像化开的糖:“不疼了。以前雷劫劈在身上,疼得想打滚;现在化成玉佩,倒能天天贴着你心口——这疼,比什么都甜。”
叶清弦的眼泪砸在玉佩上。她想起三天前江临化器灵时的模样:白狐裘染着血,龙尾断了一截,却笑着说“叶清弦,我愿意”。现在他变成了玉佩,变成了能贴在心口的存在,像从未离开过。
叶红玉的喊叫声传过来。少女扎着总角,穿着洗得发白的道袍,手里举着块用荷叶包着的桂花糕——糖霜还沾在叶子上,是山下酒肆的桂花酿做的,甜得能拉出丝。她的道袍前襟沾着黑泥,发梢却插着朵小桃花,是刚才在桃林里摘的。
“给你!”她扑过来,把桂花糕塞进叶清弦手里,“胡三太爷说,这是他藏了三年的桂花,要等你醒了吃。”
叶清弦摸着桂花糕的荷叶包,指尖沾到里面的糖霜。她想起胡三太爷从前总说“清弦爱吃甜的,要多藏点桂花”,想起去年中秋,老人抱着坛桂花酿,坐在桃树下等她,说“等你及笄,我教你酿”。现在胡三太爷的残魂还在沉砚白背上,裹在他的道袍里,像睡着了。
“红玉……”她抬头,看见少女眼角的泪痕,“胡三太爷……”
“在呢。”沉砚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背着个用道袍裹着的布包,发髻散了,白发沾着草屑,却站得笔直。布包里传来轻微的蠕动,是胡三太爷的残魂在动——老人家舍不得离开,还攥着叶红玉小时候送他的糖人。
“我带他回道观。”沉砚白走过来,指尖碰了碰布包,“用五仙阵续他的魂。当年他救过我们,现在换我们守着他。”
叶红玉扑过去,拽住沉砚白的道袍:“我要一起去!我要给胡三太爷熬药!”
“好。”沉砚白弯腰,把她抱起来放在肩头,“但你要乖乖的,不许闹。”
叶红玉立刻抿住嘴,伸手摸了摸布包:“我乖,胡三太爷要醒过来,我给他看我的新糖纸。”
叶清弦望着他们,左眼的残目里泛起水雾。她想起三个月前,红玉还挖她的右眼,现在却攥着糖纸要给胡三太爷看;想起沉砚白从前总板着脸说“道门规矩”,现在却背着胡三太爷的残魂,说“换我们守着他”。原来最动人的不是“从未受伤”,是“受伤后,还愿意一起走下去”。
“江临……”她摸着玉佩,“他们在笑。”
玉佩又烫了些,江临的声音里带着笑:“我知道。清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