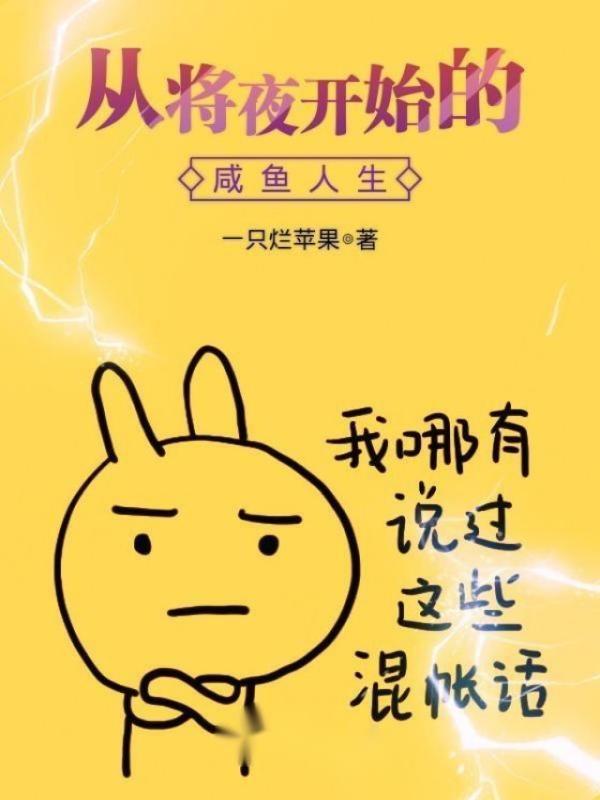紫夜小说>男朋友说他是吸血鬼怎么办怎么回复 > 第186章(第1页)
第186章(第1页)
温宁沅很慎重,“我能相信你吗?”
“信不信由圣人。”赵筠心坦坦荡荡,“臣妇只知晓这些,言尽于此,”
——
——
容述玩弄着手上的板戒,用小勺子挖着鸟食喂他豢养的笼中鸟雀,眉目很是惬意轻松。
“官家的品味就是好。”福胜盯着笼中五彩斑斓的鹦鹉瞧,满心满眼的欢喜,一双手交握着,对容述说:“圣人如果知道官家送了她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定欢喜得疯了。”
容述手上动作一停,冷冷瞪眼福胜,不悦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谁疯了?我看就是你和其他人都疯了,善柔也绝不会疯。”
福胜张大嘴巴,才意识到自己失言,连忙用手怕打嘴巴,忏悔道:“奴婢罪该万死,奴婢罪该万死……”
“听。”容述不再搭理福胜,接着喂食鹦鹉,淡声说:“你跟了我多年,我知道你是什么脾气秉性,不会怪罪于你。你是知道善柔对我有多重要的,莫要在我面前说出此等大逆不道之语,听到了没?”
福胜额头直冒冷汗。
容述是大靖的官家,在朝堂之上杀伐果断,从不受制于人,将大靖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先帝治理下的大靖边境民生凋零,是容述知人善任,命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好官治理边境,重用忠君报国的将领守卫边境,才有了如此的盛世清明。
他在容述面前一时嘴快,不小心说温宁沅欢喜得疯了,容述没有厉声斥责他,或者命宫人给他拖出去打板子,都是容述看在他自幼陪伴他的份上,给他网开一面。
福胜点头不迭,心里头对鹦鹉究竟会不会说话仍然存疑,小声问道:“官家,小小鹦鹉当真会说话吗?”
容述白他一眼,“没听说过鹦鹉学舌的典故?从前你也好歹跟着我在宫学,听到过太傅讲课,不至于这般无知吧?”
“奴婢那时在和四大王的宫人说笑。”福胜讪讪挠头,“没有仔细听过太傅讲课。”
容述不再喂鹦鹉,把鸟食甩给福胜,亲自给福胜示范:“你瞧好了。”
容述并未出声,只拿着笼中一根又短又细的小木棍,轻轻敲击笼框,鹦鹉被声音吸引住,尖叫一声。
福胜眼珠转动,心里在斟酌用词,如何哄得容述展颜。
他瞧着鹦鹉呆呆笨笨的模样,就不像是会张口说出吉祥话的鹦鹉。
下一瞬,鹦鹉嘴巴张开,用尖锐的声音朝着上方说道:“善柔,平安喜乐,一生无忧。”
福胜瞠目结舌,嘴巴张得很大,险些把下巴都掉下来了。
“官家,这——它——”福胜语无伦次,一下指着笼中鹦鹉,一下指向别处,眼睛不停眨呀眨的,很是惊奇:“它怎么知道圣人的名字?”
容述瞥他一眼,“瞅瞅你没出息的样子,我方才说了,这可是我亲自教它说的。”
“官家今日才将它买来啊!”福胜抓住重点,很是不理解:“难道它通灵性,学得非常快?”
容述摇头,视线往桌案上瞥去,示意福胜去了桌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无奈说:“鹦鹉买来后我就没有处理过朝政之事,专心致志教它说吉祥话,好能尽快带到善柔面前,博她一笑。”
“圣人若是得知官家如此用心,定会欣喜。”
福胜现在学乖觉了,其实他要说的是“欣喜若狂”四个字,害怕容述对他咬文嚼字,及时止住后面要说的话,陪笑道。
容述很是满意,扬扬下巴,说:“去坤宁殿,我要去找善柔,顺带把鹦鹉送给她。”
“是!”福胜开怀大笑,挥挥手示意底下宫人上前提鸟笼,自己默默把鸟食放至附近的桌上,用眼神嘱咐宫人收拾,连忙跟上负手前行,脚步轻松的容述。
——
——
容述来到坤宁殿时,温宁沅刚送走赵筠心。
她脑海里回想方才赵筠心的只言片语,顿时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鸣瑟劝了很久,都不能使温宁沅抒怀,被迫带着殿内的宫人们退去,让温宁沅静静。
温宁沅坐在贵妃榻上,面容变得憔悴许多,她单手撑着头,闭目靠在榻上,一闭眼,眼前仿佛出现一高大的身影,浑身散发着书生意气。
那位少年郎君,在日落后的石桥之上,对她说出此生抱负,惟愿盛世清平,百姓不再遭受流离失所之苦。
忽然,她感觉手臂被人轻轻触碰,令她浑身颤抖,整个人身子猛然一激灵,睁眼往一旁看过去。
一张俊俏脸庞出现在她眼前,那张俊脸鼻梁高挺,映着落日余晖的光,眼眸清亮又深邃,她甚至能够通过他的一尘不染眼珠里,看到两眼迷茫的自己。
她逐渐发现,那人的眼神当中充满关切,正张开双手放至在她手臂上,问:“善柔,你怎么魂不守舍的,是出了什么事吗?”
“没——”温宁沅不愿同他说起秦予维,怕他多心,道:“没事,我只是感慨近来身边人都走了自己的归宿,相继离开禁中,不能再陪伴我了,我有些寂寞。”
“有我在,我会陪伴你一生一世,你绝对不会有真正寂寞的那一日。”容述坐在她身畔,对她许诺道。
温宁沅不扫兴,点点头,很是自然得靠在容述肩膀上,“我明白的。”
容述轻轻点着温宁沅额头,用手抚平她微微的发丝,指了指福胜身后内官提着的鸟笼,轻声细语对她说:“善柔,我忙于朝政的时候,让它来陪伴你,可好?”
“好。”容述话音刚落,那只鹦鹉就又重复了先前说过的话,温宁沅忍俊不禁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