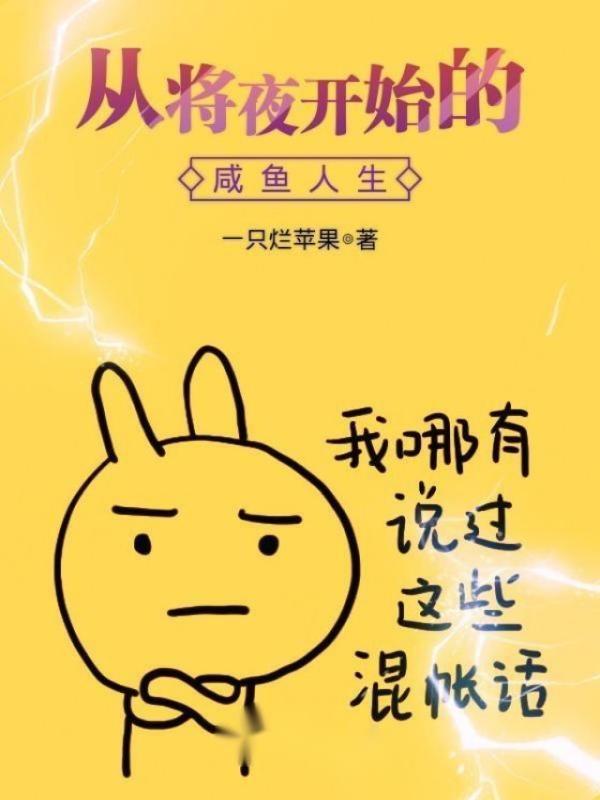紫夜小说>还想和我同棺 > 第100章(第1页)
第100章(第1页)
“第一次坐飞机?”他压低声音,带着点笑意。
应淮睁开眼,金色的眸子在昏暗的机舱里,像两点燃烧的星火。他瞥了秦骁一眼,冷哼一声:“喧闹的铁棺材。”
秦骁被他这精准又刻薄的形容逗笑了。他凑过去,几乎是贴着应淮的耳朵,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忍忍吧,陛下。等到了地方,你想怎么拆了它都行。”
应淮没理他,转头看向舷窗外。
下方,是连绵不绝的黑色山脉,如同巨兽蛰伏的脊背,在云层中若隐若现。
那股来自血脉深处的召唤感,随着距离的拉近,愈发清晰,也愈发让他心烦意乱。
秦骁看着他紧锁的眉头和孤峭的侧脸,心头一软。
他知道,这位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此刻正在为他这个“麻烦的凡人”而担忧。
夜深了,机舱里的探员们都各自找地方休息。秦骁看着依然望着窗外出神的应淮,轻轻叹了口气,站起身。
他没有说话,只是走到应淮面前,俯下身,在所有人看不见的角度,在那紧蹙的眉心上,印下了一个温柔的吻。
“别担心,”他低声说,“我命硬得很。”
应淮的身体猛地一僵,抬眼看向近在咫尺的秦骁。
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没有了平日的戏谑,只剩下不容错辨的认真和安抚。
一股陌生的、滚烫的暖意,从眉心窜起,瞬间流遍四肢百骸,让他那颗因暴怒和忧虑而躁动不安的心,奇异地静了下来。
然而,秦骁显然不满足于此。他的唇顺着眉心下滑,轻轻擦过挺直的鼻梁,最后停在了那两片冰凉的唇瓣上。
“而且,”他的声音愈发沙哑,带着一丝勾人的热气,“我还得给陛下侍寝呢,怎么舍得死?”
“秦、骁!”
应淮终于回过神,一把抓住他的衣领,金色的眸子里燃起两簇火焰,一半是羞恼,一半却是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被勾起的欲望。
秦骁低笑一声,非但不退,反而加深了这个吻,将那句即将出口的怒斥,悉数吞入了腹中。
机舱外,是呼啸的寒风。机舱内,却是无人知晓的、正在燎原的野火。
直到两人都有些气息不稳,秦骁才恋恋不舍地退开,用拇指摩挲着应淮那变得殷红湿润的嘴唇,哑声道:“等解决了那个什么狗屁山神,这笔账,我们连本带利,好好算。”
应淮剧烈地喘息着,狠狠瞪了他一眼,最终却只是扭过头,用一句压抑着情欲的“滚”,结束了这场半空中的交锋。
只是那泛红的耳根,和窗户倒影里,再也无法恢复平静的眼眸,出卖了他此刻真实的心情。
就在这时,秦骁的身体忽然一僵,他闷哼一声,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
应淮立刻转回头,神情紧张:“怎么了?”
“没事……”秦骁咬着牙,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这破石头……好像等不及了。”
他胸口,那块隔着几层衣物的龙纹玉佩,正散发出不祥的暗红色光芒,灼热的刺痛感穿透皮肉,直抵心脏。
仿佛在回应着什么东西的召唤。
进山就撞邪?这鬼地方的石头会流血!
运输机降落在西南边陲一座被群山环抱的秘密军事基地。
湿热的空气夹杂着泥土和腐烂植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习惯了北方干燥的“重锤”等人有些不适。
应淮下了飞机,只淡淡扫了一眼四周连绵起伏、如同绿色海洋般的群山,好看的眉头便几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这里的“气”,很不对劲。
基地负责人是一位皮肤黝黑、目光锐利的上校,早已为秦骁的小队备好了一切。
会议室里,当地最好的向导,一个叫盘叔的五十多岁老猎人,正叼着旱烟,在巨大的山区地图上指指点点。
然而,当秦骁的手指,点在地图上那片被标记为“未勘探区域”的空白,并吐出“悬门寨”三个字时,盘向导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他手里的旱烟杆“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被极致的恐惧填满。
“去不得!那个地方去不得啊!”他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摆着手连连后退,仿佛那三个字是什么恐怖的诅咒,“那是山神爷的地盘,是‘活人坟’!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秦骁皱眉:“老乡,我们是国家的人,执行任务。”
“这不是钱的事!”盘向导的声音抖得像筛糠,“你们不懂!每年到了那个时候,山里都会传来女人的哭声,还有吹吹打打的声音……那是山神爷在‘娶亲’!被他看上的,魂儿就得留在山里,一辈子伺候他!我们祖祖辈辈都传下来,谁敢靠近那片山,谁就是下一份‘聘礼’!”
无论秦骁和基地上校如何劝说,盘向导都死活不肯,最后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离了基地,嘴里还念叨着“别找我,别找我”。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秦骁看着地图上的那片空白,神色凝重。
没有向导,小队只能依靠高科技设备和应淮那玄之又玄的“感知”,向大山深处进发。
越野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天,最终停在了一条被藤蔓和瘴气封死的山道前。这里,就是传说中“生人勿近”区域的入口。
“下车。”秦骁下令。
小队鱼贯而入,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光线瞬间暗了下来。林间异常安静,连一声鸟叫或虫鸣都听不到,只有队员们踩在厚厚落叶上的“沙沙”声。
一踏入这片林子,秦骁就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窥伺着自己。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那块龙纹玉佩隔着作战服,传来一阵微弱的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