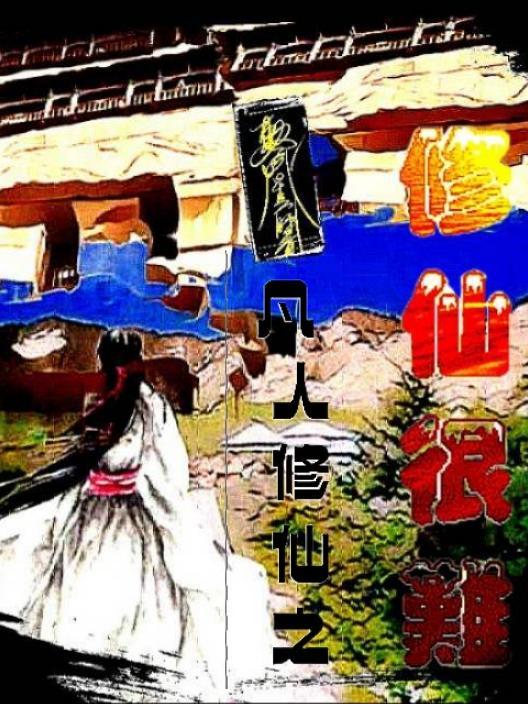紫夜小说>困住穷途 > 第38章匆匆忙忙(第2页)
第38章匆匆忙忙(第2页)
“我什麽时候赶你走了,我是给你买机票了还是找人来给你拖出去了?”
“你说让我…你说我不……”
稚稚措辞了半天才发现吕宁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让她走,她只是说自己不应该回来,但……
“你说,我说什麽了,你重复一遍,”
“……”
稚稚不讲话了,只是箍着怀里的身子,手臂不停的往里缩紧,
“别勒了,再勒我就走了,”
“你去哪!”
稚稚一下松了手,吕宁趁机转过来拉住稚稚把人带到床边坐下,
“勒死了不就是走了,给我送走,”
双手被吕宁握住,稚稚无声的摇摇头,攥着床单揪的死死的,吕宁叹口气,自从小孩回来她就一直在叹气,
“我没说要把你送走,我只是觉得你除了选择在我这以外还有更好的选择,”
稚稚的脸被迫朝向吕宁,吕宁捏着她脸颊让她看自己,一句一顿的讲,
“你才二十岁。”
都说有灵性的人眼睛是会说话的,而能做艺人的话大多数都是有灵性的。稚稚半含着泪水的眼睛像起了波澜的湖,看了一阵大风刮过,湖里便翻出很多话很多情绪,浮在水面上。吕宁最看不得别人掉眼泪,更别说正在掉眼泪的女孩子,一张水墨画一样,
“别哭了,我也没说你什麽,”
其实该说了她也都说了,剩下的,她错眼看见床对侧的玻璃上自己的那张脸,看起来真的很凶,也不怪人家哭。她努力的弯了弯嘴角,还是说了那句,
“随你自己吧。”
稚稚这才抹抹眼泪去柜子里拿风筒,抽抽搭搭的站在床边举起来示意吕宁要给她吹头发,吕宁坐好闭着眼睛听呜呜的风声,算了。
原本其馀几天是想选选去几个风景好一点的地方吃吃东西,逛一逛的,还有好多好看的好玩的没有给吕宁展示呢,可一个电话稚稚就什麽也顾不得了,而吕宁在那天晚上匆匆忙忙的订了两个人的机票。
上次匆匆忙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窗外漆黑一片什麽也看不见,吕宁在飞机上拿了毯子给稚稚盖好,又握住她冰凉的手,稚稚正窝在吕宁肩头想着什麽,睡大概是睡不着的。
电话是姜柏打的,成慈知住院了。
两个人到医院的门口已经凌晨过了,下飞机的人们匆匆散去後门口冷冷清清的,机场附近又不好叫车,半个多小时才有一辆愿意带他们去医院的出租车。吕宁从成慈知那大致知道了关于他们之前的事,也知道姜柏对稚稚大概是有敌意的,所以电话都是吕宁来打,姜柏说成慈知情况不太好,中间醒过一次,想见的人只有柯稚,他才打了电话过来。
私人医院的院子很大,她们一到门口看见两个保镖在等着了,直奔顶楼的电梯虽然不挤,在停的次数多,叮叮叮的,到了十楼以後好不容易才开始快速上升。稚稚一直拉着吕宁的手,低着头,看起来紧张极了,两个人手心都是粘腻的汗。出了门又是几个保镖,拐一个弯後才迎上来一个穿竖条西装的男人,男人精心整理过的发型现在看有点不像样子了,沾着发胶的几缕垂落在眼前,俊脸上的疲惫也一览无馀,黑眼圈重的快掉到地上,声音有些哑还带着点急促,
“来得正好,慈知刚醒,你快进去,他一直在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