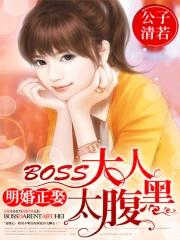紫夜小说>大明镇国公1618全文免费阅读 > 第12章 第十二章(第3页)
第12章 第十二章(第3页)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龙活虎,虎虎生威,气势非凡,万象更新。
明末通讯远不及后世便捷,当时人若要联系朋友,只能依靠书信或亲自登门,这与如今动动手指即可保存众多联系方式的智能手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李武搬入新居后,需告知几位挚友他的新住址,恰逢众人假期空闲,他便想借此机会邀友人来家中小聚,也算为主人新居增添人气。
然而,邀请并不简单,李武必须逐一登门传达邀请。
由于交通不便,他不得不将聚会日期推迟数日,以便宾客们能合理安排时间,最终定在三日后。
如此一来,大部分友人应能准时到场,主人也能及时备妥膳食。
李武骑马遍访城区多数人家,又走访了几个村庄,总算完成了所有邀约。
当他返回城中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震惊不已,直至回到家中,仍陷入深思,独自躲进房内不愿多言。
韩国公李善长及其妻女、兄弟、侄子等七十余口全被处决。
胡惟庸案十年之后,居然还能牵扯出新的罪行。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血淋淋的吗?
李武虽对朱元璋统治时期涉及广泛的“四大案”
略有所闻,也知道李善长将被清算,但如今置身其中,才深刻体会到其残酷。
这种残酷丝毫不逊于战场,甚至更加令人畏惧。
李武首次认真思考,假如自己在靖难之役中幸存,能否在未来的争中继续生存下去。
他应当采取怎样的政治立场?
李武开始仔细审视这一切。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家公司,皇帝无疑是董事长,而那些随皇帝打天下的开国功臣自然成为董事成员,至于管理日常事务的文官群体则相当于公司里的经理。
自古以来,皇帝要想稳固自己的位置并掌握较大的决策权,必须具备至少一项关键条件:要么依赖功臣,要么倚重皇族,这样才能压制高级职员,必要时也能轻松处置他们。
然而朱元璋对功臣毫无信任,大肆清洗,将儿子们安插为董事,并将他们逐出京城,以防他们制造麻烦。
在他看来,远离权力核心的儿子们不仅不会,还能彼此牵制,同时作为皇族力量约束文官集团,如此便可安心。
但他未曾料到,自家内部也会发生争斗。
当两位王爷离世后,燕王便在众王之中脱颖而出,除了东北边境无人能对其形成制约外,其余势力皆难以抗衡。
而此时的朱允炆却显得有些鲁莽,刚一登基便急于着手削藩。
削藩虽为大势所趋,也是合理的政治策略,毕竟历史上藩王引发的祸端数不胜数。
然而,他未曾深思熟虑,自古以来又有多少对削藩之事慎之又慎呢?
朱允炆手中并无功臣或勋爵可与藩王抗衡,只能依赖文臣。
可这些文臣不知出于何意,或许是受朱元璋整治过度后产生的反扑心理,又或者另有考量,纷纷鼓动朱允炆对藩王下手,丝毫不留余地。
这情形颇有小人得志的味道。
他们的这一行为,令朱元璋留下的那些功臣勋爵更为不满。
不说藩王们的配偶多出自这些家族,即便如此,这些家族本就仅存于朝堂中的这一点权力已被剥夺殆尽,如今文臣还欲进一步侵夺。
虽然他们被朱元璋压制得再无作为,但面对叔侄之间的争斗,朱允炆仍需借助他们的力量,若他们袖手旁观,岂非辜负了当初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勇气?
朱棣亦是明智之人,在获得功臣勋爵支持后,其军事行动每一步都走得稳妥。
最终登基称帝后,他不仅未对与其交战的军方人士采取杀戮,反而对文臣进行了严厉处置。
整个靖难过程,仿佛是朱允炆的一场悲剧。
朱棣借助军方功臣的力量登上帝位,因此并未像朱元璋那样进行大规模清洗。
因为他同样需要削藩,于是利用军方功臣的力量,成功削弱了宗室势力。
而文臣则逐渐收敛锋芒,专注于履行职责。
朱棣身为皇帝,随心所欲,想要征战时便可挥师沙场,除非缺钱,否则无人能够阻挡。
此阶段,武将生活颇为安逸。
然而,这样的局面若长期持续,缺乏对武将勋爵的有效约束,或许会重蹈汉末、唐末的覆辙。
但短短时日,一场土木堡之变便终结了勋爵们的统治。
文臣自此崛起,明朝后期的皇帝失去了宗室力量的支撑,也无勋爵为其撑腰,文臣集团逐步掌控朝政,五军都督府形同虚设。
朱元璋废除制度,设立的小规模内阁却发展成庞然大物。
在这种格局下,老朱家即便遇到贤明的君主尚能有所作为,而面对无能的君主则沦为傀儡。
更有甚者,许多皇帝的死亡都充满疑点。
还有聪明的皇帝将宦官势力扶植起来,这群原本只是负责日常事务的人,怎能不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李武思虑良久,深深吐出一口气。
是否有一种策略,能让宗室与功臣彼此制衡,同时又能齐心协力协助天子约束文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