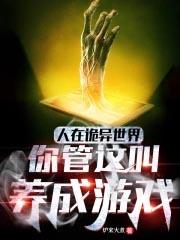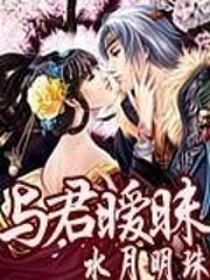紫夜小说>重回六零我带着淘宝无敌了免费阅读 > 第59章 春日新线全村人的试运行(第2页)
第59章 春日新线全村人的试运行(第2页)
“我们不接超产单,不接压价单,不接急单。”
“合作社有纪律,厂子有底线。”
这个制度一出,镇里都说:“陈家村开始像企业了。”
而村里人则说:“陈厂长开始像老板了,但比老板还讲理。”
……
某天中午,陈鹏飞刚从镇上回来,还没进院就听见厂区门口几个女工在聊天。
“你知道吗?我侄子说他们厂贴标一天只给一毛钱,我们这能记三分工,加奖金。”
“我妹在城里服装厂,一天站十小时,不如咱这里一天轻松做仨小时拿的多。”
“我家闺女也回来啦,明年她也想进来呢。”
陈鹏飞没出声,只是笑了笑,转身进了办公室。
他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让人愿意留下、愿意干、愿意信。
……
三月初,厂区开始准备第二批季节性扩产,陈鹏飞坐在办公室,看着墙上贴着的年度计划表,逐条标记、核算。
芳兰进来,手里拿着两份档案:“这是两位新报名工人,都是外村的。”
“外村的?”陈鹏飞接过一看,“一个是邻村的果农,一个是回村探亲的打工妹。”
“她们说,想在咱村干。”芳兰微笑,“问能不能报名参加‘设备实训班’。”
陈鹏飞点点头,认真写下两个名字。
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
陈家村,不只是一个村在动。
是一种方式、一种模式,正在一点点向外传开。
他抬头看着窗外,阳光暖暖地照在刚刚粉刷完的新厂房墙壁上,那几个红漆字——
“蜜果牌·陈家村出品”
已经成为这个冬天最真实的春联。
也是未来最清晰的旗帜。
陈鹏飞站在窗前,望着厂区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蜂蜜瓶和罐头箱,心中有种难以言说的踏实感。风从厂房那头吹来,带着淡淡的果香和蜜甜,那不是哪一棵树、哪一块地的味道,而是整个村子的味道,是过去一年每一双手、每一张脸共同拼出来的底气。
他转过身,对芳兰说道:“这厂建起来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我想搞‘村民持股分红制’,让所有参与的人,都能成为这个品牌的主人。”
芳兰听完,眼神一亮:“你是说……以后只要干得好,不光拿工钱,还能拿股息?”
“对。”陈鹏飞点头,“不然咱再怎么干得热闹,还是‘给人打工’那一套;咱要是真想稳住,得让大家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厂。”
芳兰想了想,笑道:“那你得把账做得更细,我女工组那边,可精得很。”
“我就等着你来盯。”陈鹏飞咧嘴一笑。
屋外的风又吹过来,吹动了门口那条写着“蜜果牌·欢迎订货”的红布横幅。
陈鹏飞眯起眼,望着这条旗子在光里飘扬。他知道,这不只是品牌的旗帜。
这是陈家村的风,是他们给自己扛起的一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