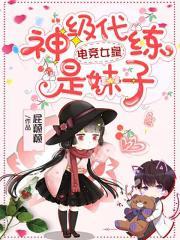紫夜小说>回到六零开网店格格党 > 第61章 品牌注册陈家村走向合法化运营(第2页)
第61章 品牌注册陈家村走向合法化运营(第2页)
他在厂区开了个小会,只讲了一句话:
“这只是块牌子,能不能立得住,还得看我们下半年是不是真能靠品牌卖货,而不是靠故事拿奖。”
众人点头。
“咱下一步准备怎么走?”陈支书问。
“搞内部评级系统。”陈鹏飞答,“以后每一批产品,都要挂上负责人的编码,谁负责贴标,谁负责封罐,谁负责检测,出了问题追得清,做好了也能奖励到人。”
“把‘脸面’变成‘责任’。”
“还要搞季度品牌讲评会,让大家都参与、都提意见,谁提的方案被采纳,年底加分加奖。”
“这不就是把厂子真的当公司来管了?”有人小声说。
陈鹏飞听见了,回头笑着说:“错了,我们不是把厂子当公司,而是把村当公司,人人是股东,个个是合伙人。”
这话一出,屋里沉默了一会,随后有人小声说:“那我们今年,还能分账不?”
“当然能,而且我保证比去年多。”陈鹏飞答得斩钉截铁。
……
四月底的一天傍晚,陈鹏飞站在厂区门口,看着一辆辆满载罐头和蜂蜜的货车从水泥路上开出村口,驶向城里、驶向超市、驶向一个更远的地方。
春风吹来,旗帜猎猎作响。
他心里忽然响起那句从前只敢在梦里说出的话:
“让陈家村的名字,不止写在地图上,也写在每一个吃过我们果子和蜜的人心里。”
芳兰走过来,把工作清单交给他:“明天还有十箱特供货要送走。”
“走得越远,咱越得小心。”她说。
陈鹏飞接过清单,点点头。
“走得远,不是靠热闹,是靠稳。”
他们都知道,这只是开始。
陈家村的牌子,才刚刚发亮。真正的路,还在未来,等着他们,一步步去走,一罐一罐去封,一滴一滴地,熬出来。
几天后,物流中心接到一通来自西安市区某连锁超市的电话,对方表示已经在展会上试销了“蜜果牌”两种罐头产品,顾客反馈良好,希望能谈长期供货,并计划在五家门店同步上架。
这个消息传到村里,像点了一把火。
“城里的超市也要咱的罐头了?”
“真的成商品啦,不是样品了?”
“以后咱进城买菜,说不定能在货架上看到咱自家果子做的罐头?”
女工组当天下午就加班到了天黑,芳兰站在灯下,一边调度人手一边盯质量。她没说一句累,但眉头紧了整整一天。
陈鹏飞找她的时候,她正在仓库里校对包装单。
“你歇会儿吧,今天干了十三个小时。”他说。
“我不敢歇。”芳兰低声道,“这是第一批上超市的货,一出问题,咱就完。”
陈鹏飞沉默片刻,接过她手里的单子:“你歇,我来盯。”
芳兰抬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些疲惫,却更多的是信任。
“我知道你不怕出错,但我更知道你怕辜负大家。”
陈鹏飞点了点头:“我怕的,是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儿,结果翻船。”
仓库外面,几个年轻的男工还在搬箱打包,嘴里哼着小调,谁也没叫一声苦。这样的场景,让陈鹏飞心里又暖又酸。
他们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可每个人都像是在做一件关系全家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