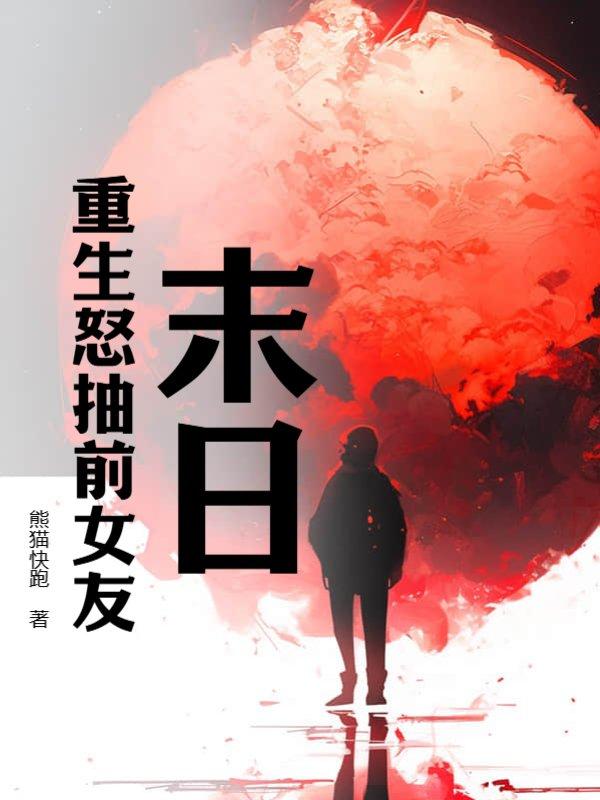紫夜小说>回到六零开网店完结 > 第54章 村企合作初步成型(第1页)
第54章 村企合作初步成型(第1页)
翌日清晨,阳光穿过薄雾洒进村子,陈家村似乎比往日更清爽了几分。
陈鹏飞一早起身,拎着一本笔记本和昨晚画到深夜的草图,敲开了大队部的门。陈支书早已在炕上喝着茶水,看到他来便招手:“来得正好,昨天书记不是说要推广咱们的经验嘛,咱得提前准备。”
陈鹏飞展开草图,铺在炕桌上:“我昨晚想了一宿,咱村要是真要推产业化,就不能光靠几个能干的工人,一定得把村企合作的框架搭起来。”
陈支书眉毛一挑:“说说看,你打算怎么整?”
陈鹏飞把纸摊开,指着一格一格的方框说:“我想建一个‘陈家村集体合作社’,由村支部牵头,我负责运营和技术,蜂场、罐头厂统一纳入这个体系。村民可以出地、出蜂、出工,按股份分红。每月对账,每季汇总,年底分利。”
“股份制?”陈支书皱了皱眉,“咱村民认这个?”
“所以得从试点开始。”陈鹏飞认真地说,“前期先选十户做示范,记录清楚收入、分红和投入产出比例,等年底分红一出,大家自然信服。”
“那万一搞砸了?”
陈鹏飞沉默了一下,笑道:“那就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锅。项目是我申请的,厂子是我带头的,我也认了。”
陈支书端着茶的手顿了顿,忽然一笑:“好,有你这句话,我放心。”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敲门声,是芳兰带着几份统计表格走了进来。
“我整理了这几天各工段的产量和出勤情况,还有蜂场那边的标签合格率。”她一边说,一边把表格摊在桌上。
“正好。”陈鹏飞接过表格,一边看一边点头,“这批橘子罐头比上批多了百分之三十出货率,而且蜂蜜标签不合格从十瓶降到了两瓶,这说明啥?大家干得越来越熟了。”
“也说明该提工资了。”芳兰轻轻一句,把两人都说笑了。
陈支书咂咂嘴:“工资这事,也得进制度。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以后每季度评定一次工分等级,高的多拿,低的也不少,谁都别寒心。”
“行,就按这个来。”陈鹏飞点头,“芳兰,等下我再写一份制度草案出来,你拿去让女工们也提提意见。”
……
午后,村祠堂被临时腾出来开了第一次“村企合作规划会”。
这场会没有任何上级干部,全是陈家村自己人:陈支书坐镇,陈鹏飞做主讲,芳兰坐旁协助,三婶刘秀华代表妇女,陈强、陈东代表青年工段,还有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代表也都来了。
陈鹏飞把手写的草案挂在黑板上,声音洪亮:
“大家好,我今天是来向大家汇报一个事:咱陈家村,要从传统农业村,走向产业合作村。我们不是喊口号,是已经干出了东西,现在要进一步——把蜂场、罐头厂、工分体系、土地分配统统纳入一个合作社体系。简单说,就是大家出一份力,就能得一份收益。”
三婶刘秀华先开口:“那咱家那几口蜂,也算股份吗?”
“算!”陈鹏飞马上回答,“你养蜂,蜂蜜进厂,我们记录下来,到年底按你家交的重量和质量分红。”
“那要是有人啥都不出,就想等分钱呢?”陈东问。
“这种人,我们合作社不会接纳。”芳兰接口,“每一份收益都得靠投入来换,我们不是扶贫,是共富。”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开始时有些嘀咕声,但到最后,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参与试点,尤其是听说年底真能分红,十户人家当场报名参与首批合作社。
“我家三亩柿子地我愿意先投!”
“我家今年分了一箱小蜜蜂,也算进去!”
“我那老梨树能结果,一百来斤,能不能也收?”
陈鹏飞把这些话一条条记在笔记本上:“咱不落一户,大家只要有心,哪怕是一棵果树、一箱蜂、一份工,咱都登记。合作社要的不是资产,是信心。”
会议结束时,芳兰低声对他说:“你这次比上次动员大会说得更流利了。”
陈鹏飞小声回:“这次说的是心里话,所以不紧张。”
……
夜幕降临,陈鹏飞回到屋里,坐在炕上摊开纸笔,重新誊写合作社章程草案。写着写着,他忽然放下笔,拿出昨天镇里刚送来的一个资料袋——里面是市里联合品牌的产品统一包装设计方案样稿。
他仔细看着那张封面,上面印着几个大字:
“陈家村·蜜果牌”
下方是工整的英文副标:“ChenjiaVillage·NaturalSweetnessfromtheMount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