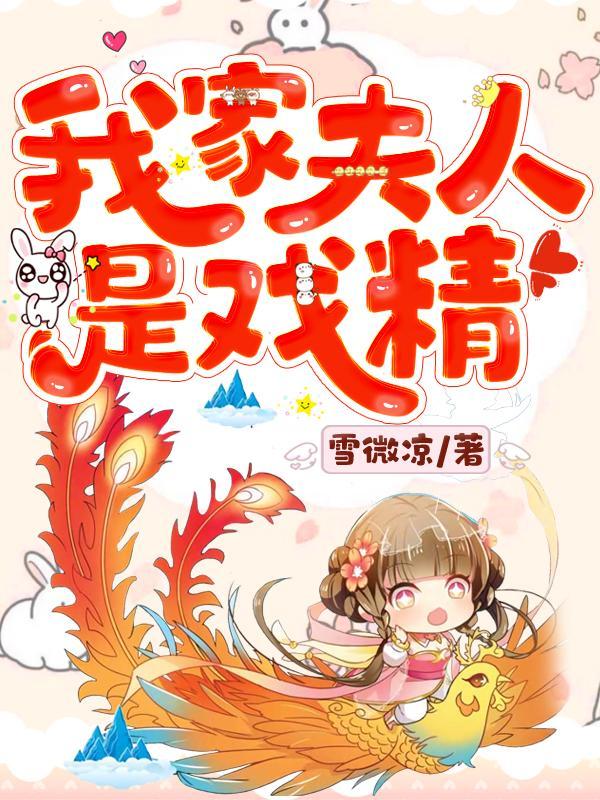紫夜小说>春季到来绿满窗图片 > 大姑丶二姑的姻缘(第3页)
大姑丶二姑的姻缘(第3页)
老娄老奶奶跟我爷爷家一墙之隔,她家的隔壁就是她二儿子家和三儿子家。这两家都有一个大闺女,分别叫做“大香”丶“大梅”,又都有一个小儿子,分别叫做“大伟”丶“大龙”。我小时候就爱和大龙丶大伟一起玩。
老娄老爷爷比老奶奶大十岁,耳朵聋了,老奶奶还耳聪目明,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听说她以前做过庄里的妇女领导,她如今在庄里依然是以她的老人家的经验丶见识和深明大义,为庄里年轻人出点子丶拿主意。谁有走不出的迷魂阵丶扒不开的麻,弄不清的风俗讲究丶说不透的伦理关系,只要找她,她很快就给你掰扯个明明白白。
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娄奶奶这样又慈祥又有见识丶又识大体的女人,真是全庄的一宝。关键时刻,老人家的见识还能救人一命。我听她说,我二姑小时候跟着我奶奶拾柴的时候,爬到树上玩。我二姑一不留神,从树上摔下来,趴在石薄连上,一动不动。我奶奶慌了神。老娄奶奶赶紧去掐她的人中,才让摔下树来的小丫头缓过气来。老娄奶奶在我心里真是神一般的老人。她可以让你安心丶定心。她不仅对乡邻友好丶慈祥大气,对她几个儿子丶儿媳妇也没听说过有什麽出格的言行。
一个村庄最具仪式感的大事怕是葬礼上的丧葬事宜了。这其中关节之多,事务之繁,不是了然于心,是不可能指挥若定的。每逢有人家里老了人,总是要来请老娄奶奶。如何破孝撕孝布,不同辈分的人戴什麽孝,三天丧葬都需要哪些环节,都是请老娄奶奶来给拿主意,老娄奶奶就是公认的主心骨儿。
葬礼上很重要的环节是一天三遍的“点汤”。一衆亲戚人等戴上孝排好队,跟着唢呐丶喇叭丶大炮的率领,沿着本庄“点汤”的小路去“点汤”。领队的是主家请来的德高望重的两位老者,他们两个擡着“汤锅”,走一段路,喇叭匠子们停下来,衆人跪下,领队的老人用汤勺子从汤锅里舀出一勺汤来洒在地上,大家起来,再继续往前走。
举行一场“点汤”仪式,要路过很多庄亲世邻的家门,会有庄里人围观。“点汤”的队伍从事主家出发,经过庄里,最後奔上家东的小道儿。一条长龙迤逦而行,小孩子们跟着跑。老娄奶奶就是这条长龙的领队。她参加了很多人家的“点汤”仪式。老娄奶奶因为年纪大丶辈分高,她很少为别人戴孝。她跟另一个奶奶一起走在队伍前头,擡着汤锅,面容庄重地走在前头。
我特别敬服老娄奶奶。她的为人也是大气得体,没有一点小家子气。她是明朗的,准备赐教和指引的,她的存在并不是只惠及她自己,而是同时也惠及其他人的。
我见过很多次“点汤”,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掩盖她的光芒。跟她一起“点汤”的人站在她的身边,无论是气质丶长相,还是见识,都只能是她的陪衬。她是那样沉着丶坚定,万事了然于胸。她又那麽慈祥慈悲丶襟怀坦荡,见解正确,时刻都能让人醍醐灌顶。
我现在还记得跟她一起“点汤”的徐姓大爷爷,他稳重老实,谦逊低调,他也同样跟老娄奶奶一样走在队伍前面,但是他在我心目中并不能胜任一个领袖的头衔,他不像老娄奶奶那样辉煌伟岸。
我在庄里看见过很多葬礼。那些葬礼的形式和人员也都是大同小异。只有一个人的葬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老温爷爷的葬礼。
老温爷爷是一个秃子,这是年迈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他叫老温。但因为他得过一场瘟疫而变成了秃子,我总觉得他的“温”是“瘟疫”的“瘟”。老温身体孱弱,精神不济,有些邋遢。他不常出门,蜗居在家,出门也是拄着拐杖,脑门油亮丶面红耳赤,低头哈腰丶气喘吁吁,像个天宫里的仙翁,像赤脚大仙吧。他家在南荆堂最南边,淹没在一长遛儿的麦稭垛里,叫人很难看到他家的真容。他的大儿子如意四十多岁,没有婚娶,只有一个领养的女儿叫温丽丽,温丽丽常跟我玩,有银盆似的有红似白的大脸,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如意是个典型的劳力,他胡子拉碴,忙于劳作,整张脸被晒地红黑油亮,像块打蔫了的猪腰子似的。
如意要去干活,温丽丽跟着老温奶奶。
有一天,久未露面的老温奶奶居然带着温丽丽来庄上卖豆芽子来了。老温奶奶也是孱弱的身体,气若游丝的嗓子。她穿着灰白的带大襟的褂子,花白的头顶上,戴着一顶绒面的黑帽子,远看观近看都像是一个男版的济公和尚。她手里拎着的孙女温丽丽,像是她拄着的一根拐杖。
老温奶奶一手牵着温丽丽,一手提着装豆芽子的塑料黑水桶。在大街上走走停停。知道的,以为她是卖豆芽子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个老乞婆呢。看到她,北荆堂的几个妇女凑上前去跟她搭话。
“恁来卖豆芽子的,大娘?有阵子没看到你了?你身体还怪壮实?”家业大娘凑上去说。家业大娘手里也领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也叫丽丽。她叫宋丽丽。
宋丽丽是北荆堂的,她是家业大娘的长房长孙女。家业大爷兄弟五个,如狼似虎,在南北荆堂也算是高门大户。家业大娘才五六十岁,成天把丽丽揽在怀里。丽丽长地白白胖胖,粉粉嫩嫩,双眼皮丶大眼睛。一衆人见了家业大娘抱了她来,都围着她,来逗她玩儿。丽丽靠在奶奶怀里,安安详详丶尊尊贵贵,接受大家的朝贺。大嫂子是长房长媳,也同样受人尊敬。大嫂子人长得矮小,个子不高,脸蛋像枯黄的树叶一样单薄。坐席的时候,婶子丶大娘都招呼她。“她大嫂子,这个菜没有荤油,你能吃!”“她大嫂子,这个肉,不是猪肉,你也能吃,多叨点儿!”大嫂子是“胎里素”,不吃肉。大夥儿都知道,所以对她格外关心。
“我来卖豆芽子的,恁嫂子。”老温奶奶说,“我还怪好。”
“恁牙口儿什麽的还好吧,大娘?”那些婶子大娘问她。
“我牙口儿还行。”老温奶奶说,“多亏了俺二儿丶二儿媳子。人家过些天就来看看我,还给我送节礼,给我买吃的。啊,我吃的豆奶粉。”她张开嘴给人家看。
“那可不孬。大娘。自从俺二兄弟到了张庄,人家过得可好了。人家老岳有本事,开着面坊。二妹妹还给你生了两个孙子儿。”家业大娘说。
“两个孙子儿都不姓温。都姓张。”老温奶奶说。
“什麽姓张姓温的。都是咱的血脉。一个姓,那还不是无所谓嘛。”家业大娘说。
“是的。恁嫂子。俺想得开。俺家恁二兄弟也想得开。弟兄三个就数他过得好。”老温奶奶说。
“丽丽也跟着恁奶奶来卖豆芽子的?”家业大娘问她。温丽丽躲在奶奶的手里,不说话。她的脸上抹地黑一道,白一道的。头发油油地贴在额头上。家业大娘手里的宋丽丽仰着白白的大脸,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她。
“啊,丽丽也跟着我卖豆芽子的。俺的叫丽丽。恁的也叫丽丽。”老温奶奶说,“俺叫温丽丽,恁叫宋丽丽。”
“都是丽丽!”家业大娘笑着说,“俺是北荆堂的!恁是南荆堂的!”
“恁这个孙女子长得可不孬!双眼叠皮儿的。”老温奶奶笑着说。
“恁孙女子长得也不孬。有红似白的。”家业大娘说。
“俺没时间照顾。如意儿要去干活儿。我年纪大了。还得照顾她爷爷。”老温奶奶说。
“行,大娘,有苗不怕长。丽丽长得不孬,从小被你理持地又懂事儿。以後找个好人家。俺大爷身体怎麽样了?没看到过俺大爷嘛。”家业大娘说。
“他走不动了。都七十九了。过天了日了。我不是来卖这点豆芽子,我也不出来了。”老温奶奶说。
“能动弹的话还是勤出来走走。走走身体好。”家业大娘说。
“行!恁嫂子。我再走走了。”老温奶奶说着提起了她的水桶。
同样是丽丽,同样的雪白粉嫩,同样的大眼睛双眼皮。北荆堂的宋丽丽因为有爷爷奶奶丶爸爸妈妈的庇护,尽享尊荣。南荆堂的温丽丽却孤寒落魄,虽有个老光棍儿的父亲,和一个年事已高的祖母,但在别人眼里,形同孤女。
出身高贵的,人家看她的眼光也尽显尊贵,什麽事儿都高看她一眼,觉得她浑身都是一副高贵的皮囊,怎麽看怎麽让人欢喜。久而久之,她在别人眼里也越发贵气和傲气;出身卑贱的,人家看她时也觉得她低人一等,觉得她天生就是一副贱命。久而久之,她在别人眼里也就一股子寒酸气。
“俺爹啊!俺可怜的爹啊!你怎麽死了的!你一辈子没享过福啊!”
一个下午,我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嚎啕大哭着从家东进了庄。她哭着从竹来大爷的小店前拐过去,直奔南家前而去。
“老温死了!”我爷爷似笑似不笑地看着我说。
刚才哭的女人是老温的二儿媳!是了,老温的二儿子入赘去了张庄,找了一个开面坊的人家的闺女。
那女人如今也是三四十岁的年纪,她生地白净面皮,身後跟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年长十七八,沉稳老实丶白净秀颀,像他斯文沉稳的爸爸。二儿子年幼又顽皮,颜面像他的妈妈。她的老实斯文的男人推着一辆洋车子一声不吭地走在她的前面。
老温二儿子一家子来荆堂奔丧了!
这个可以确定平时跟老温鲜有接触,更甭提有什麽感情的二儿媳,一进庄东头儿就开始嚎啕大哭。她哭地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她煞有介事地哭着她的公爹。这是一种仪式,也是庄上人早就约定俗成的规矩,痛哭和眼泪,都是规矩。
出殡前,最後一个大型仪式,是“行路祭”,场子搭在大街上。棺材搁在路中央,两旁站着男女老少,这些人自然地围成一圈儿人墙。他们肩挨着肩,头挨着头,看着逝者的亲朋好友,在一个主事的男人的号召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自己的项目。主事儿的点到谁的名字或是一辈人的名字,被点名的那个人,或是那些个人,就上台进行“路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