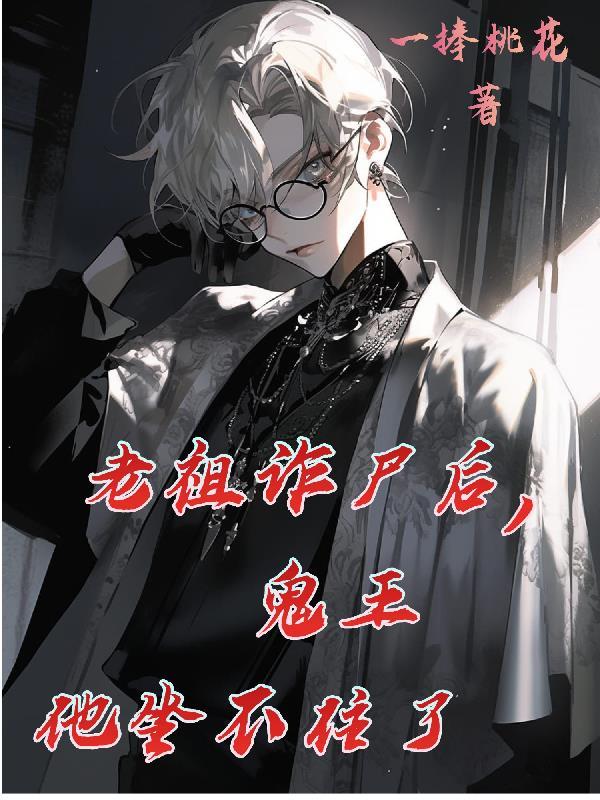紫夜小说>和宿敌穿进校园文扮情侣 > 第 30 章(第3页)
第 30 章(第3页)
明明才刚过来,还没住进去,这间空寂已久的屋子已经沾染了他的气息,带着一种冷冽的侵略性,慢慢往外蔓延。
夙音的腰不自觉後折,弯成了一个极有韧性的弧度,方才逃脱掉那种被包围的诡异实感。
这副画面怎麽看怎麽诡异。
她维持着这个姿势,仰头,认真地说,“我对你的房间不感兴趣。”
“我对你这个人比较感兴趣。”
谢凌序微妙地顿了下,“是吗。”
“是呀。”夙音纯良一笑,白皙皮肤上两点痣黑的晃眼。
他移开了目光。
屋内,工人默默捂住耳朵。
他什麽都没听到。
其实刚才夙音是在观察谢凌序的衣柜——几乎都是黑色的衣服,要说现代这个谢凌序和那位正道魁首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穿衣颜色了。
那人永远是正道标配的一身白衣,不竖冠,只用一根白色发带扎起最简单的马尾,出剑时,发带会晃起与剑式一样凌厉的弧度。
夙音曾无数次想抽下那根发绳。
然後用它勒死他。
可惜这个愿望到底都没有实现。
这里的谢凌序是短发,不需要发带了,这里的谢凌序也不是那个想勒死的人了。
夙音盯着他,有些恍惚,来这里不过短短几日,曾经深恶痛绝的身影竟然也模糊了起来,转而替之的是这张一模一样,却不那麽令人厌恶的脸。
“院长,已经整理完了。”
工人的话打断夙音的回忆,她做贼一样飞速低下头,复又悄悄看了那个立在旁边垂眸不知道想啥的人一眼,搬起马扎给人家让出了一条路。
谁知工人刚走出房门,刚才还一动不动的人瞬间移动,反手关上大门。
带着清冽气息的门风凉嗖嗖地扇在了夙音脸上,发丝飞舞,她下意识闭上眼,只听见一声金属啪嗒,门被锁了。
“这麽防我还来我这儿住?”她下意识吸吸鼻子,重新睁开眼睛,看向门旁的男人。
谢凌序将钥匙收回口袋,随意道,“不希望某天晚上再看到自己床上长出一个人。”
夙音撇嘴,小气鬼,这麽记仇。
“放心,不会长出来,肯定不会再长出来。”
还没走远的工人再次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他啥也没听见。
……
从医护楼回来的那一刻,小护士感觉自己天塌了。
不过出去俩小时,回来发现顶头上司搬进了自己的工作地点。
这就意味着,她以後要天天在院长眼皮子底下上班,不论做什麽都会被院长看在眼里,即使小护士问心无愧,但是这种压力,谁顶的住!
夙音看她魂都飞了,出声安慰:“想开点,起码你的很多活可以扔给他干,反正他才是主治医生。”
小护士抹了把辛酸泪,把工作甩给院长,她敢吗?
当然不敢,她只敢更小心地工作,“那院长之後要和少宗主一起用餐吗?需要提前问喜好和忌口吗?”
“不必。”谢凌序的声音突然从背後传来,插入对话。
“不用准备我的份。”
住进来对双方已是勉强,何必再互相折磨。
小护士下意识回头,院长出现在背後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她一颗心高高提起,听到内容後又如释重负地放下。
还好刚才没说院长坏话。
以後就要习惯随时可能会出现的院长了。
夙音靠在岛台上,托着腮,“怎麽,愿意跟我一起住不愿意跟我一起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