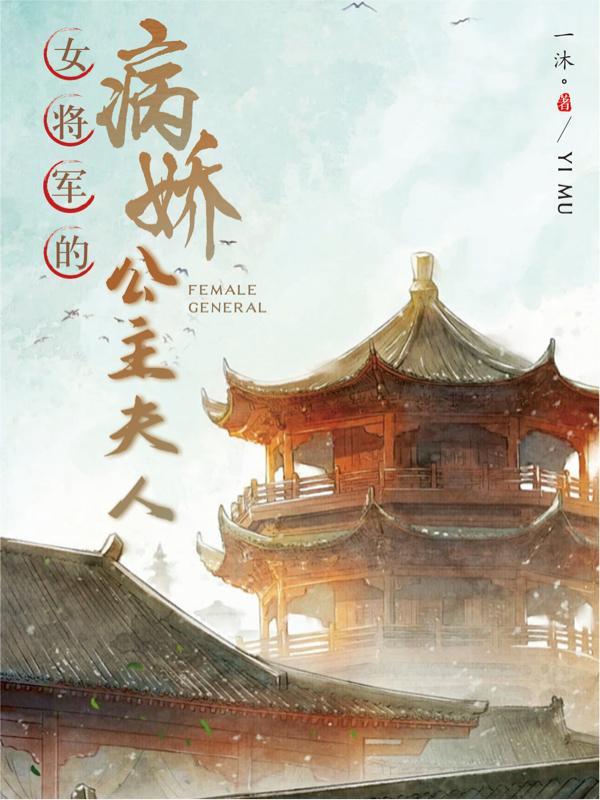紫夜小说>被天子一见钟情后 > 第36章 第36章 待陛下择妃我出宫已修添(第3页)
第36章 第36章 待陛下择妃我出宫已修添(第3页)
魏清砚却笑了起来,“娘娘瞪人的模样,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想起国公夫人那一巴掌,他不是因为那个巴掌才幡然悔悟,才察觉自己对棠棠不好,是那个巴掌叫他知晓,有些话该及时说才对。
尽管不合时宜,也该及时说才对。
他遂慢慢道,“臣向来没有大志向,自幼被逼着读书,读得再好也未想过科举中状元。”
“妻子知晓臣的难处,从未要求臣上进,去考什麽状元,臣想着就这样和妻子一直过下去。”
“後来,臣以为妻子厌弃了臣,才和臣和离,臣也不知挽留,以至于铸成大错。”
魏清砚想起乔棠执意要和自己和离时那双执拗眸子,他拧不过乔棠,同意了。
乔棠抹掉眼泪,将和离书朝他一扔,“你自己去衙门办去吧!”随即出了温府,再也没有回来。
他自己去了衙门,拿着和离书,路过茶肆,看见乔棠和旁人闲聊,笑起来明媚娇妍。
他心想,原来棠棠离了我,这般开心。
“没过几日,镇国公府找到了臣,母亲恼怒温家对臣的凌虐,可怜臣,要让温家绝嗣,臣同意了,故作坠崖而死。”
从此世间再没了温璟这人了,乔棠不知缘由,在崖下寻了许多日,魏清砚自得知後,每每想起了,都悔恨不已。
“是臣犯了很多错,才到这般田地。”
可是——
跨马游街的状元郎,镇国公府二公子,才情卓绝的魏编修,哪个都不是魏清砚想要的。
镇国公府并不知晓,他们每每和魏清砚说不可失态,不可情急,要徐徐图之时。
魏清砚都想说,他只是僻远冀州一个商户苛待养大的温璟,不是京中高门望族中,处事有度冷静自持的世家公子。
他的冰冷,他的淡漠,让京中朝堂误以为他端肃冷静,实际上这只是他的坏性子,他想做的不过是——
魏清砚看着乔棠,昔年床榻间转头就能吻到侧颜,如今一道隔着不可逾越的天堑,多麽令人绝望。
可他慢慢笑起来,“也许有一天,臣能带着妻子,回冀州去。”
回冀州去……
乔棠在心里咀嚼这几个字,原来他还在期待着已不可能发生的事。
却说静仪郡主忍着羞怯自文华殿出去,带着宫人行了一路,立在路边,紧张地绞紧帕子等着。
没成想,却等来了李公公,她见李公公焦急地步过来,正疑惑着,听李公公道,“陛下要见郡主,请郡主随奴才去一趟。”
静仪郡主只好去了,原以为得去勤政殿,不想又行了一会儿,在半道见着了裴承珏。
她瞥了一眼,心头哆嗦,只觉这位堂兄与往常不一样了,浑身透着股阴鸷,声音也是冷的。
“你与魏清砚一事,可想清楚了?”
静仪郡主咬唇,她正犹豫不决呢,不知如何答,忽瞥见裴承珏袖下手指摩挲着一副小像,瞧那模样,应是惠姐姐。
若是搬出惠姐姐,这位堂兄兴许就不这麽催她了吧,她遂道,“贵妃娘娘正在帮臣妹问询魏编修意见,臣妹想再等等,听听魏编修的答案,臣妹恳请陛下……”
“惠贵妃在文华殿?”
裴承珏沉声掐断她的话,她不由点头,裴承珏眉峰骤拢,撇下她往文华殿去。
文华殿,屋檐雪水嘀嗒不停。
乔棠低眉,看着魏清砚俯身捡落地面的书籍,默然不语。
魏清砚起身,抱着书靠近长案,将书籍一一在长案上放好。
两人距离近了。
魏清砚看着她泛红的眸子,轻颤的睫羽,极快地垂下眸子,“臣适才说了多麽多,娘娘可还要劝臣应下与静仪郡主的婚事?”
乔棠摇摇头,这桩婚事成了,最後伤得最深的只会是静仪郡主。
她看着长案上的书卷,思及静仪郡主中意魏清砚的理由,心生悲哀,那姑娘倘若知晓自己钟情魏清砚的地方竟是魏清砚厌恶之处,不知会是何滋味。
“本宫会劝陛下放弃这桩赐婚。”
魏清砚将书卷整好,唇角一勾,微微笑起来。
这笑离太近了,乔棠看得怔然,她想,原来连魏清砚都会变,会笑得这般好看,会讲很多的话。
若是三年前,他便是这样,她自成亲就得到了想要的,还会和他和离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