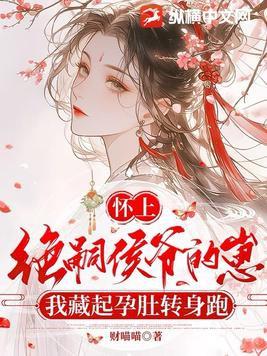紫夜小说>千秋宴是什么意思 > 第七十三章 马失前蹄(第2页)
第七十三章 马失前蹄(第2页)
舟歧回帐後,独坐在帐中沉思,他想了许久,从一腔愤懑到不甘落败。
帐外的水声依旧,传入舟歧耳中,却使得他无比厌烦。
思量片刻,他决定再战一番,洗雪耻辱。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月间,他先後设下多个计谋,却一一被玉云二人看破,致使败无可败,不得已只能率部逃回县中安歇。
一日休养中,舟歧在屋中收到了南王的旨意,意在斥责他贻误军机,识敌不清,故而将他降了一级,贬为司马,舟歧自知理亏,也甘心领受,未曾料到,这时,兵卒带来了一个消息。
“将军,方才末将在屋外久战,听那驿使说,此事是卓相邦的授意。”
“嗯?卓岚到底想做什麽?”
舟歧想了想,忽然明白了过来。
此前在大殿之上,他所说不过奉承之语,意在让陛下以为他与卓岚有同好之心,故而疏远于他,此次贬斥他,更是在趁势铲除异己,他向来厌烦荒野之人,只将他们当做草原上的野人,又哪里会生出什麽好意……
舟歧想到这,不免心生厌烦,他推开门,走向门外。
从前跟随他的五十个部民已折损了一半,经历了多场战役,剩下的二十几人也身负重伤。
舟歧走着走着,身後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司马。”
那人唤了一句。
舟歧回头,见是陆忠。
“明忠兄…”
他垂下眼帘,冷言道:“明忠兄是来看我的笑话吗?”
陆忠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我知今日局面,并非全然是你之误,你已然尽力了,其实南国之灭,只在早晚而已,此事需天和,更需人和,岂是因一人而能转圜的?”
“我不明白,为何仪国能够轻易取胜?”舟歧问道,心中仍有不甘。
“一个国家的灭亡,总是从内部开始分化,而後才是外部,当徐国丶靳国丶禹国在因为朝廷之事吵的不可开交,专心权术之时,仪国上下却是同心协力,为国解难,同样,百姓也是一样。”
“你是说……”
“南国的百姓已然不相信南国能够取胜了,只将希望寄托于神灵,可能庇佑百姓的,从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灵,而是百姓自己,我曾经听过一个大逆不道的言论,敢于做‘反贼’的,是为勇气,敢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是为英雄。”
陆忠转过身子,叹道:“我的先生曾经便做过这样的人,他说,若官无道,百姓当举起兵器来反官,若君无道,百姓当凝聚在一处推翻君王之位,自然,他这番话在旁人听起来自是大逆之言。”
“况且,强权之下,百姓多有牵绊,又岂能怪罪于他们?”
舟歧听後,叹了口气,说道:“明忠兄,你说了这麽多,我到底没听出究竟为何?若我再不能取胜,恐怕我的这些弟兄性命也难保。”
陆忠说道:“而今仪军势大,就算我使出百般计谋助你,也不过拖延一时,你可曾想过,仪国今日之盛源自何处?”
“兵力?”舟歧问道。
陆忠点了点头,说道:“仪国征战多年,作为君王,仪王难道不知连年征战,会致使百姓负担加重吗?仪国曾与禹靳二国休战两年,足以见得他也是明白的,可他依旧要这麽做,为的是什麽?”
“他为的,是再无後顾之忧。”
“而帮他达成这一局面的,是萧玉悲,是玉子骁,是一衆文臣武将,是他们,共同铸成了一切。”
舟歧仿佛明白了他的言下之意,便点了点头,说道:“歧此前多有得罪,今日谢过明忠兄提点,歧明白了。”
陆忠瞧了他一眼,觉得他并未明白过来,却透着一股自信与得意。
他刚想再说些什麽,舟歧便快步而去,神态飞扬,仿佛看见了一道灼光。
入夜之时,舟歧披上蓑衣,低声在二十几个部民中间说道:“而今我之去,是为大计,待我铲除奸贼,势必要让仪国灭亡。”
“等我回来,再一同喝一壶酒!”
“老大,您这一去,叫弟兄们怎麽办才好?老实说,弟兄们也待够了,想当年咱们在草原上,那是何等快意?醒了放羊,醉了便睡,如今入了军营,处处受制不说,还要遭人冷眼。”
“是啊,老大,您何不带着咱们一同去呢?也好让那两位将军相信。”
“………………”
舟歧想了想,说道:“说的也是,我只身前去,只恐他们不肯相信,只是……万一脱身不成,岂不是连累你们?”
“我们不管,只跟着您就是了,上刀山下火海,哪怕死在仪军刀下又有何妨?”
“是啊,老大,您可千万别丢我们啊!”
“老大!!!”
舟歧看着衆人眼含泪光的双眼,不觉叹了口气,他站起身,说道:“那待我留下书信,以免叫人误会,以为我是真心投敌。”
“至于你们,且先在对岸处等我,等我无恙,再出言请仪军去接应你们。”
“好,那我等便在此处等待。”
舟歧点了点头,随即来到岸上,他乘着一叶扁舟,晃晃悠悠的离开了衆人的视线,大雾将他的身影吞没,看不出他的踪迹。
不知过了多久,水波之中忽然出现了些许划痕,衆人擡眼望去,见是仪军的船只。
坐上船只後,他们瞧见了大片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