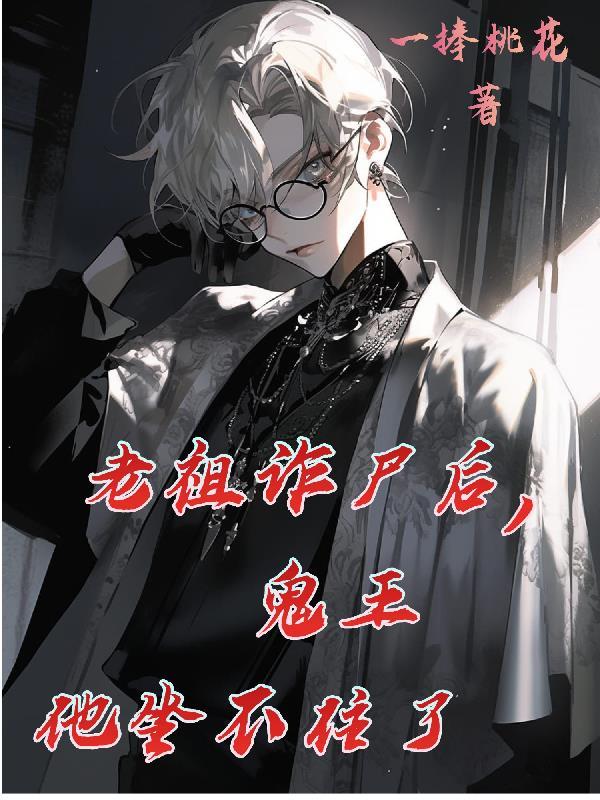紫夜小说>死不瞑目以后会复活吗 > 树目3(第1页)
树目3(第1页)
树目3
王敬成预备结束他最完蛋的一天。
他哆嗦着手从内兜翻出四方的红烟盒,如饥似渴地塞进嘴里,水和饭救不了不愁吃穿却失魂落魄的男人。
火苗不安分地在穿堂风中来回跳跃,黄中泛青的脸跟着忽明忽暗,昏花的眼睛里头也有热气在冒,熏得眼眶通红。
蛇吐信子般,在烟被两根手指夹着暂时脱离唇瓣,空荡荡的嘴巴大大地吸气,发出绵长的“嘶”音,混进灰白的烟雾与其徐徐上升。
从很久以前开始,发生的不幸就像多米诺骨牌般不断码下去,一块接着一块,直到第一块向後倾倒,从前往後,牵连着最後一块生命仰倒,现在它依旧躺在地上,冰凉的尸体停放在他冰凉的双脚之间,涣散的瞳孔直直地对准烟雾中朦胧的脸。
我好像做错了什麽,但一定不都是我的错,该死,真该死,就倒了一次霉醉了一次酒而已。
妻子前些年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哭着闹着要离婚,谁知道呢,新婚燕尔,喜得贵子,襁褓里的孩子撕心裂肺地啼哭,狠心的亲妈却不哄,她气得胸脯上下起伏像吸气漏气的气球,连日的怨念最後进的比出的多,谁知道呢,当时她真的生气了,明明之前还算通情达理。
老母亲含辛茹苦地给他养大,哪有儿子把妈拒之门外的,她不是才当了妈吗,怎麽不知道体谅体谅丈夫的拳拳孝心。
想起来女人尖利的骂声和哭诉,最後是漠然阴凉的目光,他晃了晃脑袋难受得厉害。
摔门声震耳欲聋,搞忘记是谁先退出房间又是谁独自坐在床边,吵架的两个人停止了无意义的争辩,意识到沟通无用的事实。
谁知道呢,平时好好的女人说翻脸就翻脸了,一口咬定要带走他的儿子。
“儿子儿子儿子,你老王家就了不起,从我肚子里一爬出来就完全变成你们家的了。我可是记得,你们怎麽把我当成下崽的动物,动物!这麽想要啊?自己生啊。我不会再变成一次动物,就这一次。”只有一次。
女人站起来,吊灯晃动的阴影盘踞在面无血色的脸上,他们分别有不同的脸。
一个永远蒙在烟雾中路看不清楚他他看不清楚路,一个直愣愣地挺在黑暗里像睡着了,可等一挪到阳光下,他又会发现妻子疲惫的双眼始终怒目圆睁。
女人看清楚自己的路,把看不清楚的迷雾扔到他头上,转身就走,步伐越来越快,怀里抱着他的儿子,老王家的独苗苗。
没了。
前些日子她以高高在上的口吻发来通知,去给儿子改名。
仗着一时之利挟持走了珍贵的人质,然後没给任何时间就要撕票了?
老母亲知道了还不得闹翻天。他们家的天最近简直翻来又覆去,父亲在的时候母亲温柔和蔼,父亲一死就像吃到肉的绵羊,立马无法忍耐只吃草的日子了,她饥肠辘辘,几十年来的草忽然不管用了,嘴唇翁动,必须要嚼点什麽。
到嘴的媳妇跑了,那可是心心念念的肥肉。
“儿啊你没有个体己的人在身边妈放心不下,妈要是看不到你完成婚姻大事妈死不瞑目。”
不是的,她真正想说的是:你爸把我嚼了很多年,妈被嚼的只剩丝丝缕缕的纤维,妈老了虚弱到必须补充生肉的时候,你给妈带一块肉,临死前我好歹过一次嘴瘾。
王敬成也饿,和母亲时而发作的不同,它更会潜伏,爆发起来叫人猝不及防。
“我只是一时糊涂,喝醉了酒看走眼,她身上的裙子我妻子也有件一样的。”他哪里仔细分辨过女人家的装束,就记得黑颜色红花图案。
那天女学生来找他签字。
快放长假了,一看那女的签完字就要出校门去跟哪个毛头小子约会,化着妆背着小包。
“同学你等我找找源文件。”
她先把手撑在桌子上後面好像觉得不太好就平放下去,等的过程中感到无聊,便自以为隐蔽地移动桌下的脚。
硬质的鞋底抵住办公室的地面,缓缓擡起来,小腿肌肉绷紧,过了一会儿再放下,然後重复以上动作,自创了和缓而疏解困意的抖腿慢动作。
款式时新的裙子花纹却是旧的,受文艺复古风格的影响,和十几年前的流行相差无几。
他边慢悠悠地滑动屏幕,馀光中黑色的幕布褶皱时多时少,鲜艳的小花图案上下纷飞。
一节大课正好结束,教学楼那边刚下课的学生叽叽喳喳地走出来,闹得人头晕。
哦,头晕的原因可能还包括昨晚心情不好喝了酒。可能来办公室之前也喝过,他记不太清。
翻文件翻到前妻的头像,也是花花绿绿的,俗气。
旁边裙子上的图案万花筒一样转开了,女学生偏过头专心致志地听楼底下的闲话,也许在找男朋友过来没有,一时不察没注意收敛解闷的小动作,真的开始抖腿。
你——
她错愕地倏忽扭过头,没有说话但眼睛里明晃晃地质问着完全没预料的冒犯。
尖利的女声再一次响起来了,比前妻吵架那次还高亢。
毕竟她年轻,能敏锐地感知到上风口传来的危险味道,以及及时做出反应。
就是这样,事情忽然就完蛋了。
没人相信这番说辞,因为他离婚多年,这也是为什麽他反复想起来前妻的原因——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从前往後,从第一块开始倒塌。
“嘶。”王敬陈深吸口气,如痴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