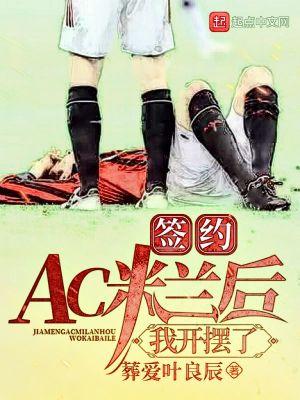紫夜小说>瑰心心理情感咨询 > 陷落恐惧 离开了十八年的父亲他回来(第1页)
陷落恐惧 离开了十八年的父亲他回来(第1页)
陷落恐惧离开了十八年的父亲,他回来……
原来绑匪不止要钱,还要灯博的镇馆之宝。
也难怪,当年程家已经计划要卖房子,最後却没有卖,因为就算卖了,也起不到关键作用。
“我爸妈知道这件事吗?”程斯宙问。
“除了警方,我们谁都没告诉。”林信摇摇头,拭去眼角尾纹渗落的残泪。
“为什麽不说出来?明明那麽重要的线索。”
“你还记得,当年的灯博吗?修复室和库房是一片连着的平房,外边有一圈栅栏围着。那时候条件不好,安防也没那麽先进,尤其安仪出事那段时间,库房後门还坏了一扇,随便一推,就能闯进去。”
程斯宙那会儿还小,记得库房,但不记得後门长什麽样。
文物库房通常很有讲究,比如现在都是两道门,需要两名保管人员同时开锁才能打开,而且整个区域布满监控,外人想要偷点什麽,那是不可能的。
“门坏了没有报修吗?”程斯宙问。
“申请打上去了,要层层签批,领导签字,才能拿到经费,拿了经费才能找人来修。”林信回答。
程斯宙在灯博上了六年班,他明白,任何涉及到钱的事都是这麽个流程。
“修复组临时拿材料补了补,还不敢补得太明显,不然让有心之人发现,进去偷走几样,他们管库房的丶搞安保的,包括领导都要受牵连,轻则丢工作,重则要坐牢。”林信继续道。
“所以不透露,是不想让人觉得,瓷簋很值钱。”
“是啊,我们报警之後,电视台啊,报纸啊,一下来了好多记者,如果我们实话实说,反而给了别人动歪心思的机会……”
“那年灯博没失窃过吧?”程斯宙想要再确认下,“他们最想要的,到底是钱还是瓷簋?如果是瓷簋,勒索不成,他们会去偷吗?”
“没有,除了安仪丶除了我的安仪,什麽都没有丢……”
听着师娘低低的呜咽,程斯宙眉心拧痛,他有一个不敢深想的猜测,几度盘桓却没有说出。
他的师父蒋韵礼,向来把责任看得比天大,若那时,文物的安危和女儿的性命被放在天秤的两端,他是有可能选择保护文物,而放弃女儿的。
但这对于师娘来说,实在太过残忍,既然师父没有明说,他也自当缄口不言。
“师娘,他们只索要了这一件文物吗?”
“是,只要这一件。”
“师父有没有说过,这件特别在哪?”
“它是龙脊山出土文物中,最有分量的一件。”
盘问师娘绑架案的细节,不仅是在折磨她,也是在折磨程斯宙自己。
他握住林信的手,长长舒了口气,那些乱七八糟的线索,终于连起来了。
子川的父母曾被困于龙脊山碑灵村,但没有条件发掘古墓。
他们回来後,闻铎打越洋电话联系了某个国外团夥,三年後,古墓被盗,张馆长率领的考古队恰好发现盗墓团夥踪迹,却没来得及阻止,最後仅带回一樽破碎的紫金釉六耳瓷簋,修复完成後,收进了馆藏。
盗墓团夥发现少了这一件,得知瓷簋即将展出,就以绑架勒索的方式逼迫灯博交出来。
陈年往事盘根错节,程斯宙推敲了数遍,仍然觉得,哪里不对。
“师娘,您确定是闻铎联系了国外的盗墓团夥吗?会不会只是巧合?”
“绝不是巧合,我英文虽然不好,但亲耳听到绑匪说了个词,奥米特。”
“奥米特?omit?遗漏丶省略……?”
程斯宙在脑海中构想,盗墓团夥进入古墓的场景。
他们应该带走了墓中最精美的陪葬品,但因为六耳瓷簋意外摔碎,所以被认为没有价值,就故意遗漏了它,对吗?
然而一年半後,灯博修复组耗尽心血将瓷簋复原,他们竟又想着,以勒索的方式拿走?
这帮混蛋,实在太过厚颜无耻了!
“所以他们知道,瓷簋不是单独一件,而是一批文物中,被遗漏的一件。当时连考古研究所都不清楚,除了瓷簋,古墓里还有什麽!你说除了闻铎,谁会那麽了解古墓,会把瓷簋的消息透露给外国人?!”
林信说到这里,程斯宙已经没有任何语言来应对。
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自己是理性占了上风,还是感性占了上风。
尽管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就是闻铎向外国盗墓团夥提供了消息,但毫无疑问,他的嫌疑最大,程斯宙也没有办法证明,不是他干的。
可闻铎是子川的爸爸,假如真是因为他,导致安仪无辜惨死,他们能不顾一切地找到闻铎,让他血债血偿吗?
阁楼外大雨连绵,程斯宙凝视着雨幕,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要说恐惧,这场茫茫无尽的大雨早已将闻子川拽进了恐惧的深渊,好像有人勒住他的肚腹,死死摁进了水沟里。
整个肺部都像浸饱了水,一个完整的呼吸都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