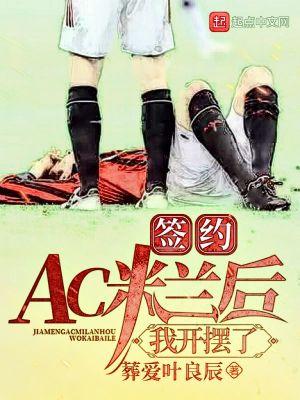紫夜小说>嫂嫂万福重生 七六君 > 第55章(第2页)
第55章(第2页)
“武埠山地处大魏西北关口,本属大魏战略要地,现又已探得异族人潜入,便就更应由朝堂管辖治理,才能庇佑边州之安。”他还有理有据,令天家缘由充分地成为武埠山铁矿脉的辖主。
萧景琰也没想到裴远山这一介莽夫,不见三日,已精进至此,言辞间已滴水不漏。
更让他心中不爽利的,是裴远山竟然全然成了王昭云的发言人一般,完全不顾王昭云是不是真的发现过矿脉。
萧景琰与王昭云自幼相识,他了解她,她不可能不知道这山上全是铁矿。
萧景琰心底涌动,但面上却不能作出任何起伏。
这一场博弈中,他要的是铁矿,而不是她。
他佯作若有所思半晌,才点头接受裴远山的说辞,“裴将此言甚是在理,待孤回往天都,必定如实向圣上禀报,再做定夺。”
武埠山虽有丰富的矿脉,但地处偏远的西北,即便朝廷有心管之,只怕也是鞭长莫及,所以,哪怕是太子也不可能在当下就说将矿脉归为天家所有,否则,只怕又会惹来世家的争闹。
裴远山对此亦深知然,但面上却不去揭穿天家所处位置的窘迫,只附和道:“如若有臣能帮得上忙的地方,还请圣人和殿下尽管下令。”
萧景琰再无言,便令江观风将武埠山风貌全然记入采风记。
待一行人回至军营,已临近落日十分。
王昭云的侍从正在大帐外急如热锅的蚂蚁,惶惶已有盏茶功夫。
自从新春大宴之後,裴远山解了营中对所有王家人的限制。
但春娘特别交代,姑娘去往钱庄之事不可惊扰他人,尤其是天都来的太子殿下。
于是,这小仆便只能暗暗等在营中,盼着能单独相告于姑爷。
然裴远山闻之立马惊怒:“怎麽此时才来报?”
他差点就同对待手下士兵一样,要甩去一鞭。
但到底是忍住了,免得又要让那个自以为是的妻子说他鲁莽。
可鲁莽的明明就是她。
她是才治好了上武埠山落下的伤,这下又要去另一个虎xue?
裴远山听罢小仆一言,立即就上马扬鞭而去。
尚在军营门口。交办事项的太子与江观风吃了一口的沙,却怎麽也叫不回一支离弦的箭。
“裴将军怕是有什麽急事,才没来得及同太子殿下告退。”江观风小心地观察着萧景琰的神色,一边斟酌着词句为裴远山开脱,“奴见边州事杂又多,每每都是要裴将军亲自出面处理,总要叫他忙得不可开交,将旁事放置一边的。”
萧景琰抿着唇,也不知有没有将江观风的话听进去。
他起先还是半眯着眼,做打量的神色,但不过一息,唇角就起了浅浅的笑意,无头无尾地说了一句江观风听不明白的话——“这下,他是真的有得忙了。”
*
边州城区,钱庄。
即便布下天罗地网,王昭云也没能如愿活捉那个所谓天都来的线人。
到底,那个要当面以对的人并未出现。
他早早布下层层叠叠的障眼法,然後骗得王昭云一衆前来,又折腾了半日,才将将在钱庄後院寻得信封一个。
“一封信而已,寻个童子递来不是更加干脆?何故弄这些玄乎?”春娘将信封呈上,嘴里在念叨,凝眉在思索。
王昭云的脸色也不见得好。
她捏着信封一角,撕得极慢,还自言自语一般,呢。喃着,“此人用的墨家连环阵,虽云里雾里绕了几重还有些不甚顺畅的地方,但到底已经比阿娘用得要精密十分。”
她几乎不敢相信,当世竟还有人能比阿娘更懂墨家术。
忖度间,信封被撕裂,信纸露出来,其上最为显眼的不是擡头单一个“溪”字,而是铺面而来的熟悉感——是阿娘的字迹。
王昭云急急将信纸抽出,落款处果真是阿娘的名讳,单一个“云”字。
她粗略看过信中所言——原来“溪”是尹溪,“云”是谢云,原来“青溪”是两人名字的相合。。。。。。原来十年前的大混战中,镇北军军败如山倒,是因阿娘为边州所设防城器械图被人暗地篡改,以至于不能防住胡贼进攻,而篡改人是。。。。。。王昭云的父亲。。。。。。
王昭云惊得几乎不敢再看。
她急急翻过一页,却见赫然几个大字“裴家大郎,无留活口”,落款单一个印玺。
那印玺,王昭云认得出来,是父亲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