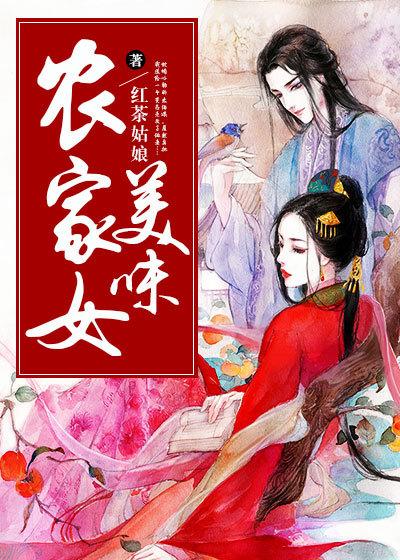紫夜小说>豺狼失控日志在线观看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
结束之後沈欢问他有没有空着的卧室可以洗澡。孟子羡回答得下一层楼。沈欢伸手在背後扣上胸罩扣子,说那算了。过了会儿,她说我的裙子破了,被人看到怎麽办。
他牵着她下楼时经过好几个眼熟的人,沈欢垂着眼睛,不敢和人对视。好在那些人也目不斜视,装作没看到她。
快到一楼大厅,脚下的地毯变成泛凉的大理石地面,沈欢回过神来说我的鞋还在楼上。孟子羡擡起左手晃了晃拎着的高跟鞋。沈欢从他手里接过,两下子套脚上。他说你不该再穿高跟,孕激素上去了容易摔跤。沈欢拉了把裙摆,她问你哪来的冷知识。孟子羡正经严肃地说我刚在梅奥上查的。沈欢笑着擡头,看见他低着的侧脸。他浅淡的瞳仁里罕见地有些无措,一晃而逝,她再看去,还是那双深邃而强硬的眼睛。
他们开车回杰里科的路上,沈欢声称她晚上一查到医院给的李斯特菌的报告,就上来告诉他。孟子羡在红灯停车丶挂空档,侧过头看她,看了一会儿,他转回头看着前面的路,并不相信她。
沈欢洗澡的时候,孟子羡从客厅玄关的抽屉里取出格洛克,卸下弹夹和子弹,放进二楼的保险箱里。长岛的治安环境比起法耶特好很多,把枪上了膛放在能快速拿到的地方只是他的习惯,沈欢不喜欢,他会做出改变。
卧室里他在她身後搂着她睡觉,摇粒绒睡衣让她抱起来像是个毛绒玩偶。他低头把鼻子埋进她头发里,是柑橘和温热水蒸气的味道。静了一阵,沈欢问,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他嗯了声。
她心里先过了一遍措辞,发觉没有什麽更婉转的方式。她问他为什麽不戴十字架了。
孟子羡想了一会儿,“最後一次去达瓦什的时候丢了,没找回来。”
“不可以新买一条吗。”她背对着他问。
他有一会儿没说话,身後只传来沉缓地呼吸。沈欢想可能不该提这个问题。她怕触及了什麽他心底埋得很深的伤疤。
但孟子羡还是回答:“丢掉的不是十字架。”
他音色里的滞涩让沈欢眼眶发酸。她问那是什麽。
他说是信仰。
安静半晌,沈欢开口:“说起你最後一次去阿富汗,我一直想和你道歉。我不该在那时候不打招呼地搬走。你们在外头卖命,我至少该等你回到班尼堡,当面给你一个理由。但是我害怕等你回来,我会离不开你。”
这话令孟子羡的呼吸凝固了,在卧室的黑暗里僵直片刻後,他问:“你现在可以给我个理由吗。”
沈欢像是被问住了,她的身体蜷得紧了些,摇了摇头,“对不起。讲这个让我很难过。”
孟子羡伸手把被子盖上她肩膀,他没再说什麽。
到了後半夜沈欢又把他推醒,她把被子踢开,贴到他左侧,侧身躺着,脸对着他,下巴搁在他的肩膀,擡着头看他,眼睛睁得老大。
她说:“讲起信仰,我搬走以後,爱玛说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
孟子羡屈起左臂把她圈进怀里,闭上眼,哑着嗓音问几点了。
沈欢执着地问:“爱玛在短信里写:‘YouarethesinglemostfaithlesspersonthatIknowof。’是不是这个意思?”
孟子羡睁开眼,皱眉沉默了一会,终于说道:“她很没礼貌。”
沈欢呆了一阵,“是吗。”
孟子羡点头,“如果她还活着,我会叫她和你道歉。”
沈欢的眼泪掉下来,“可是她死了。”
孟子羡转过身抱她。
沈欢把脸埋他胸口,“她还没和我道歉。”
清晨六点孟子羡去海边跑步,回来时看到赵啓的车停在车道里。孟子羡拧开矿泉水瓶,喝了口水,往後院走。
赵啓在他身後跟上来,问他有没有看到《时报》的托克·阿克曼发来的factcheck邮件。
孟子羡说看了。阿克曼问孟子羡在滨南管教中心那一年是否与一名狱警发生过激烈冲突,造成了狱警颈椎脱位的严重伤害。
赵啓说这老小子近两年拿不到什麽跨境企业内部的正经素材,总像个小报记者似地搞花边新闻。
孟子羡从後院的棚子里拎出铁铲和金属灰桶,蹲在火盆边上,轻手轻脚地清理木炭灰。他说你声音小点。
赵啓整个人僵了一下,合上嘴,半佝着脊背弯下腰,在孟子羡耳边压低声音问咋了,有人监听吗?
孟子羡蹲开一些,他说沈欢在睡觉。
“噢。吓我一跳。”赵啓舒了口气,直起身,把领带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