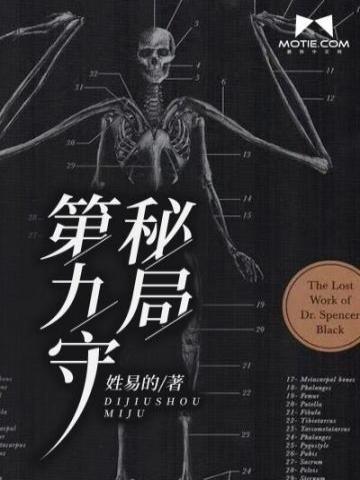紫夜小说>日本歌曲荒城之月 > 第三回 食野兔稚子遭折磨 失八哥弱身犯旧疾(第1页)
第三回 食野兔稚子遭折磨 失八哥弱身犯旧疾(第1页)
第三回食野兔稚子遭折磨失八哥弱身犯旧疾
又过两日。
据此地十馀里的太平乡有一老爹上山采药,摔下山崖,伤势严重,动弹不得。家人连夜翻山越岭来请孙太医。孙仲行带着孙牧,匆匆赶去了。
易水和易寒兄弟俩闲着无聊,去後山猎来一只山鸡,两只野兔。就在院坝外生了一堆火,将野鸡和兔子架在火上,烧烤起来。不一会儿就烤得外焦里嫩,肉香四溢,勾人馋虫。
瓦舍几人围着火堆,割腥啖膻。
萧平舟拿来一壶酒,骆孤云伤势未愈,尚不能饮。萧平舟和易寒兄弟便一人一盅,喝酒吃肉,谈天说地,好不欢快。
瓦舍何曾这样热闹过,萧镶月十分开心,跟在大人後面,忙进忙出,蹦蹦跳跳,天真无邪的脸上挂着纯净的笑容,乐得屁颠屁颠。
宋婶来给火堆添点柴火,易水满上一盅酒,双手奉上,恭谨地道:“我们兄弟三人多有叨扰,婶娘辛苦。这杯敬婶娘。”
宋婶羞得满脸通红:“大侄子客气。。。。。。婶娘不会喝酒,还是你们喝罢。”
萧镶月来凑热闹:“婶娘是女子,不能喝酒,月儿代婶娘喝罢。”
宋婶一巴掌拍开他:“小孩子家家,喝什麽酒。”仰头将酒一口喝了。
衆人哈哈大笑。
萧镶月平常吃的都是寡淡的药膳,何曾吃过这麽美味的烧烤,又是好奇又是垂涎。那鸡肉常吃倒不稀奇,尝了口兔子肉,觉得又嫩又香,很是美味。骆孤云见他爱吃,便拿着一只兔腿,小块小块地撕肉给他,不知不觉,竟吃了大半只兔腿肉。
萧平舟趁着酒兴,拿出随身的一管玉箫,在篝火旁幽幽吹奏起来。那箫声如怨如慕,婉转回旋。萧镶月侧耳倾听了一小段,道:“爹爹奏的是《浪淘沙》。”便随着箫声,唱合起来。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清澈纯净的稚嫩童音,合着如泣如诉的箫声,在夜空中缓缓流淌,竟是说不出的凄凉肃杀,勾起人的满腹愁绪。骆孤云心想,萧平舟痛失爱人,客居异乡,自是心绪烦闷,故总做这悲凉之音,可这些词曲对小孩儿来说,究竟是太沉重了些。。。。。。一时衆人都沉默了,周遭万籁俱寂,只闻篝火的噼啪声。
萧平舟见衆人默然,哈哈一笑:“怨我怨我,好好地竟扫了大家的兴了,来。。。。。。喝酒喝酒!”举起酒杯和易水易寒兄弟相碰,一饮而尽。
骆孤云也举杯与萧平舟相碰,陪饮了一小杯,道:“先生才情高绝,重情重意。在这乱世之中傲然有风骨,淡泊致远,小侄钦佩。”
衆人对酒当歌,相谈甚欢,至亥时方散。
夜半时分,骆孤云写了会儿字,正准备躺下歇息。就见对面屋子掌起了灯。萧平舟急急地出屋,来到正房,叩了几响门,低声唤道;“嫂子,嫂子!月儿不好了,大哥他们有没有说何时能回来?”骆孤云一惊,连忙披衣下床。
进到西屋,就见萧镶月小小的身子侧躺在床上,拼命蜷缩着,脸色青白,额上冷汗直冒,牙关紧咬,显是在忍耐极大的痛楚。易水易寒也被惊醒了,大家围在萧镶月床前,均不知为何晚上还好好的,怎麽突然就这样了。
“哎哟,这可如何是好!偏巧爷儿俩都不在,也不知啥时候能回来。。。。。。”宋婶急得直跺脚。孙太医父子出诊,遇上病情严重的,留宿是常事,路途远一点的,两三天不回来也是有的。
“莫非是吃坏了肚子?”想着晚上的烧烤,易水猜测。
“睡觉前月儿就说有点不舒服,我先也以为是吃坏肚子了。给他服了些和胃散,谁知反倒越来越严重,刚刚还疼得在床上打滚。”萧平舟一手搂着蜷成一团的萧镶月,一手给他擦拭不断冒出的冷汗,着急道,“再说吃坏肚子应该又吐又泻才对,但这些症状都没有。”
听到父亲的声音,萧镶月睁开眼睛,睫毛轻颤,艰难地开口:“爹爹。。。。。。月儿没事。。。。。。没事。。。。。。不疼。。。。。。”
骆孤云见萧镶月的身子在父亲怀里不住地颤抖,显是难受极了,却紧咬着下唇,不肯呼疼,也不肯发出一点呻吟,反倒是来安慰父亲,心里也是疼惜。走近前去,摸了摸萧镶月的面颊,触手冰凉,又见他面色惨白,嘴唇乌青,竟像是中毒的症状,心下一沉。当即道:“看这症候,怕是不能耽搁。孙大叔去哪里出诊?能寻到麽?大哥二哥,要不你们骑马去太平乡,问问大叔在哪家看病,若寻到就赶紧接回来。”
这当口宋婶已经去马厩牵出马匹,道:“你们不识得路,我去寻。”
易寒道:“黑灯瞎火的,嫂子一人上路不安全,我们一起去罢。”
三人快马加鞭,消失在夜色中。
屋里,萧平舟紧搂着萧镶月,面色沉重。骆孤云拧来毛巾,给他擦拭不断冒出的冷汗。
萧镶月犹在强自忍耐,身子蜷成一个虾米,双目紧闭。极力抵御着痛楚。萧平舟心疼道:“月儿,疼就喊出来罢,别忍着。。。。。。”
萧镶月轻唤:“爹爹。。。。。。冷。。。。。。月儿好冷。。。。。。”
骆孤云伸手一摸,孩子背上的冷汗把里衣都浸湿了。已是初冬,夜晚寒意袭人,冰凉的衣服贴在身上,大人都受不住,何况孩儿?当即道:“我去生个炭盆,一会儿屋里暖和了给月儿换身衣服。”
萧平舟点点头:“也好。”随即又道:“还是我去罢。月儿闻不得碳烟味,每年冬天取暖用的碳都是用栗木,在烧制的时候特殊处理过的。去年还剩着好些,放在竈房的隔间,怕你寻不着。”把萧镶月移到骆孤云怀里。叮嘱道:“贤侄看顾好,别让他伤到自己。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咬破舌头都不肯哼一声。。。。。。”
骆孤云搂着怀里的小人儿,只觉身子轻飘飘的,一点重量都没有。汗湿的额头上一缕头发贴在额角,浓密纤长的睫毛在灯光下拖出长长的影子,映在白瓷般的面庞上。眉头紧蹙,气息微弱,精致的五官秀美绝俗,竟不像个真人,像那画里的纸人。见他紧咬下唇,伸手轻抚面颊,想让他放松。
萧镶月觉察到触感,以为是父亲,呢喃道:“爹爹,月儿冷。。。。。。你抱抱月儿。。。。。。”骆孤云紧了紧手臂,埋首将脸贴在萧镶月冰凉的面颊上,久久未动。
炭火升起,屋子里暖和了些。萧平舟找来亵衣,又端来一盆热水,给萧镶月仔细擦拭换洗。脱了衣服,萧镶月的身体看着更是瘦骨伶仃,半两肉都没有。这孩子。。。。。。也太瘦弱了。骆孤云直皱眉。
次日清晨,易水三人才把孙太医接回瓦舍。
孙太医翻身下马,未及站稳就冲进屋,捞起一只手给萧镶月把脉。在路上他就仔细询问了情况,心头已有大致判断。一摸脉象,更是证实了他的猜测。
“快,仙鹤草丶土茯苓丶半边莲丶白蔹。。。。。。三碗水煎成一碗,给月儿服下。”孙太医快速开出药方,吩咐随後进屋的宋婶赶紧煎上。孙牧还留在那家尚未返回。
“这。。。。。。月儿到底怎麽回事?要紧麽?”萧平舟看孙太医开好方子,缓过一口气,忙开口问道。
孙太医长嘘口气,懊恼道:“都怨我没有给你们交待清楚,害月儿白白遭了罪!月儿最近吃的方子里有橘皮丶山参,这两味药。与那兔肉最是相克,合在一起无疑就是毒药。轻则头晕丶腹痛,重则抽搐昏迷。唉。。。。。。”孙太医内疚不已。
“不怨爷爷。。。。。。都怪月儿贪吃。。。。。。”被疼痛折腾了通宵的萧镶月虚弱地躺在床上,微微侧头,半眯着眼睛,小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