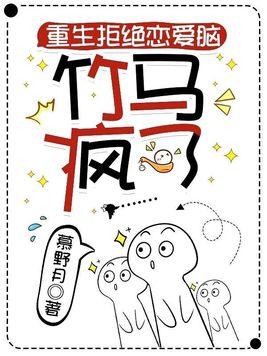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诡异医生百度百科 > 第83章 圣赎之城番外 少年领着温音穿过走(第5页)
第83章 圣赎之城番外 少年领着温音穿过走(第5页)
看来是自己这具身体还算争气,熬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风寒。
她轻轻舒了口气,有些庆幸,又有些失落。
正当她准备起身找点水喝时,房门被轻轻敲响,玛莎大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走了进来。
“醒啦?感觉好些了吗?”
玛莎将粥放在床头,关切地打量着她。
“昨晚埃米达说你这边有咳嗽声,我们还有些担心,看来是没事了,脸色好多了。”
温音接过温热的粥碗,感激地笑了笑:“谢谢您的关心,应该是没事了,只是着了凉,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
玛莎大婶看着她确实恢复了不少精神,也放下心来:“没事就好。”
“嗯。”温音轻轻点了点头。
-
因着这场病,温音获得了暂时的优待。
大家都叮嘱她好好在房里休息,不必出来帮忙。
她乐得清静,却也觉得有些无所事事。
白天里,她只远远透过门缝,瞥见过迦希尔一次。
他正穿过庭院,与一位年长的信徒低声交谈着,侧影在雪後初晴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挺拔沉静,却也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
他并未看向她这边,仿佛昨夜那个模糊梦境中的纠缠,真的只是她病中的一场臆想。
收回目光,温音轻轻合上门,回到小榻边。
左右无事,她的目光落在了墙边那个简易的书架上。
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些宗教典籍和普通的书籍,看起来经常被人翻阅。
她随手抽出一本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用普通硬皮装订的手写书册,信手翻开。
然而,只是看了一眼,她的心跳便漏了一拍。
那纸页上的字迹,清瘦丶有力,带着一种独特的风骨,与她记忆中迦希尔书写时的笔迹……一模一样。
时光似乎在这一刻倒流。
那些在吉拉镇的小屋里,看他记录日常的片段……所有关于他伏案书写的记忆,都因这熟悉的字迹而变得鲜活起来。
他保留了过去的书写习惯。
这个认知让温音心中泛起一丝微妙的涟漪。
她有些心绪不宁地合上书册,指尖无意识地拂过耳後,总觉得那里似乎有些异样。
仿佛被什麽东西轻轻烙了一下。
犹豫片刻,她走到房间角落那个有些模糊的旧铜镜前,微微侧过头,借着窗外透进的光线,看向镜中自己耳後与发际线交界的那处。
镜面模糊,但她依然清晰地看到,那里有一小片不甚明显的暧昧红痕。
颜色很淡,但形状却……像极了被人用力吮吸後留下的印记。
昨夜梦中,那滚烫呼吸烙在颈间的触感,那低沉喑哑的,仿佛贴着她耳廓响起的声音……猝不及防再次涌了上来。
温音僵在了镜子前,只有耳後那处微小的红痕,仿佛带着未散的体温,将她的心脏烫得一阵狂跳,几乎要撞破胸腔。
许久之後,她才勉强平复呼吸,仔细整理好微乱的衣襟,深吸一口气,拉开了房门。
-
走廊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只有从祈祷室隐约传来的诵经声。
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隔壁那扇紧闭的房门。
那是迦希尔的卧室。
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驱使着温音推开了那扇未锁的门。
房间里的陈设简洁得近乎刻板,符合一位神父应有的清苦。
但温音却捕捉到了一些几乎无法察觉的细节。
书桌一角摆放的墨水瓶,是她记忆中他惯用的那种特殊款式。
椅背上随意搭着的一件旧袍,袖口的磨损痕迹与她记忆中他某个无意识的小动作完全吻合。
甚至空气中混合了特定书墨与冷香的气息,都像极了她记忆中的味道。
温音的视线最终落在了书桌中央,那本看起来最为陈旧的皮质笔记本上。
她颤抖着手,翻开了它。
映入眼帘的,不是经文,也不是教义笔记。
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