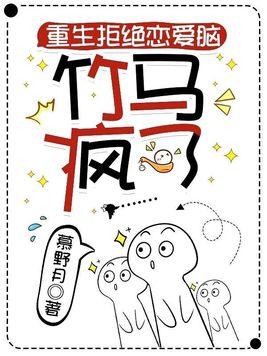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诡异医生百度百科 > 第83章 圣赎之城番外 少年领着温音穿过走(第6页)
第83章 圣赎之城番外 少年领着温音穿过走(第6页)
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用炭笔丶墨水,甚至可能是指甲或是什麽尖锐之物刻划出的……属于她的画像。
有她托腮远眺时微微出神的侧影;
有她被他逗弄後娇嗔含怒的眉眼;
有她在破碎晚霞中决绝离去时,眼角滑落泪珠的瞬间;
那些早已被她自己遗忘的神情姿态,都被极其精准捕捉,并定格在了这粗糙的纸页上。
纸张因频繁的翻动而显得软塌,许多画像的边缘因无数次指尖的摩挲而变得模糊。
甚至有些页面上还残留着疑似干涸的水渍晕开的痕迹,如同无声的泪。
温音眼眶有些发酸。
直到她翻到靠近後面的一页,那里不再只有画像,还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字迹时而工整,时而狂乱,仿佛记录着书写者截然不同的心境。
她的目光死死锁在最後一行,那用几乎要划破纸背的力道写下的字句上:
【第32个雪季,她终于归来。】
【以我最渴望的模样,判我永远沉沦。】
手中的笔记本险些滑落。
原来……他记得一切。
记得她的模样,记得他们的过往,记得那场分离。
所谓的“亡妻”传闻,或许只是他拒绝他人丶封闭内心的借口。
而他白日里那温和的疏离,不过是一层薄冰,掩盖着其下翻涌了三十多年,几乎能将她吞噬的炽热岩浆与深沉痛苦。
他一直都在看着她,以他自己的方式。
而她,却像个傻瓜一样,以为他早已将她遗忘,甚至为那个莫须有的亡妻黯然神伤。
巨大的震惊混合着汹涌的心疼,如同海啸般将温音淹没。
她扶着桌沿,才能勉强站稳,耳边只剩下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
就在她心神剧震,几乎无法思考之际。
一种被注视的强烈感觉猛地攫住了她。
温音泛红的眼眶里还噙着未来得及落下的泪水,她下意识地回头。
迦希尔就静立在房门处。
他不知是何时出现的,依旧穿着那身纯白的神父袍,身姿挺拔。
金色的发丝在窗户透进的逆光中,晕开了一层模糊的光晕,让他大半张脸都浸在阴影里,看不真切。
他微微垂着眸,目光落在她手中那本摊开着的,写满了他所有隐秘妄念与痛苦的手札上。
在温音尚未从这突如其来的对视中回过神来时,迦希尔动了。
他并未向她走来,而是微微侧身,伸出手,不疾不徐丶极其从容,擡手将门内侧那根老旧的木质门栓,轻轻推入了卡槽之中。
“咔哒。”
一声轻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清晰得令人心头发颤。
没有惊愕,没有质问。
迦希尔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门边,逆着光,如同一位降临在忏悔室中的,沉默的神祇。
可那周身弥漫开来的,不再有丝毫掩饰的深沉气场。
以及那由他亲手落下的门锁,却让温音瞬间明白。
那层温和慈悲的表象,那看似遥不可及的距离,不过是精心维持的幻象。
三十二年的时光并未消弭任何执念,只是将炽烈的火焰压成了冰冷的暗涌。
此刻,暗涌终于冲破了堤坝。
她站在他私密的罪证前,耳後还残留着他的印记。
空气凝滞,无声宣告着:
审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