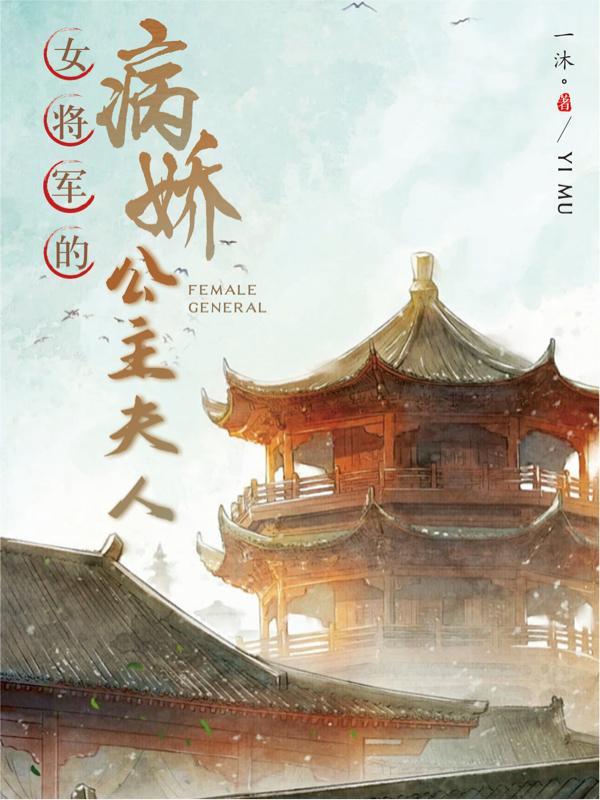紫夜小说>不失所望 > 55(第2页)
55(第2页)
求你松手,放开我。
妈妈……不能呼吸了,快放手。
可是妈妈的脸却消失了,程抒晴捂着他的口鼻,表情和当年跪坐在地上的母亲如出一辙。
“阮牧年,”她一字一顿道,“我当初,就不该喜欢你。”
某股巨大强烈的情绪从心底破土而出,或许它早已蛰伏在那里,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
而现在正是那个时机。
阮牧年猛地後撤出一段距离,呼吸有些不稳,垂在身侧的手指控制不住地微微抽动。
他感觉自己张开了嘴,可能说了一些委婉的话,程抒晴疑虑的表情渐渐缓和下来,甚至还点了点头。
但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什麽。
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麽跟程抒晴告别,有没有去请假,又是怎麽走回家的。
身体和意识好像被割裂成了两个部分,第一扇门里的阮牧年游刃有馀地处理着这些琐事,第三扇门里的阮牧年意识模糊,浑浑噩噩。
路过茶几的时候,还被绊了一跤。
身体重重砸到地上时,某些意识才忽然回笼,他下意识蜷缩起来,慌乱地去查看手臂。
可现在是冬天,层层长袖包裹着,他根本伤不到。
但那里的皮肤还是一阵阵地跳着痛,像是已经长疤的陈年旧伤被重新翻出皮肉,鲜血顺着划口一点点滴下。
他想大喊一声,却还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怎麽回事?
他砸了砸地板,没有声音;将纸巾扔到窗户上,没有声音;脑袋磕到了茶几边缘,没有声音。
他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耳朵,企图能听到一丝真实的声响。
没有。
没有。
什麽都没有。
耳内只是循环播放着男人的怒吼,女人的尖叫,盘子的破碎,以及被捂在掌心里压抑的啼泣。
他好像被困在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场景里,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压抑和恐惧重新升起,一点点剥夺他的听觉,他的呼吸,乃至意识。
而他所有的挣扎都被那只庞然大掌压下,连同他的哭泣声一起,泯灭在无尽的绝望中。
怒吼丶尖叫丶哭声。
男人丶女人丶孩子。
一遍,一遍,又一遍。
一遍遍濒死,又一次次生疼。
眼前是一片白茫,是天花板的颜色,还是妈妈俯身时遮住他双眼的衣襟?
身上好疼,是摔到地上导致的,还是妈妈紧抱他时勒出来的?
面前黑一阵白一阵,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觉,只有如影随形的恐惧一如既往的真实,攫住他所有的意识。
那句表白又钻进他耳里,每一个字眼都引得他灵魂颤栗。
“牧年啊,我其实……挺喜欢你的。”
不要对我说喜欢。不要。
我早已预见了喜欢的结局。
是面目可憎的男人,歇斯底里的女人,以及她怀中快要窒息而亡的婴孩。
他逃避了这麽多年的恐惧,最终还是降临了。
但程抒晴是第一个,绝对不是最後一个。
总有一个人的喜欢他会接受,然後迈向那个令他恐惧丶令他抗拒的既定结局。
总有一天。